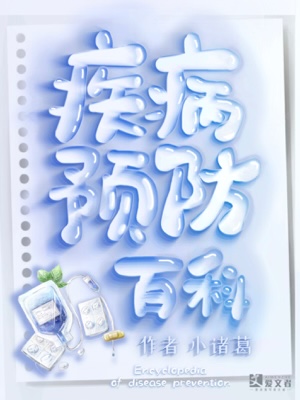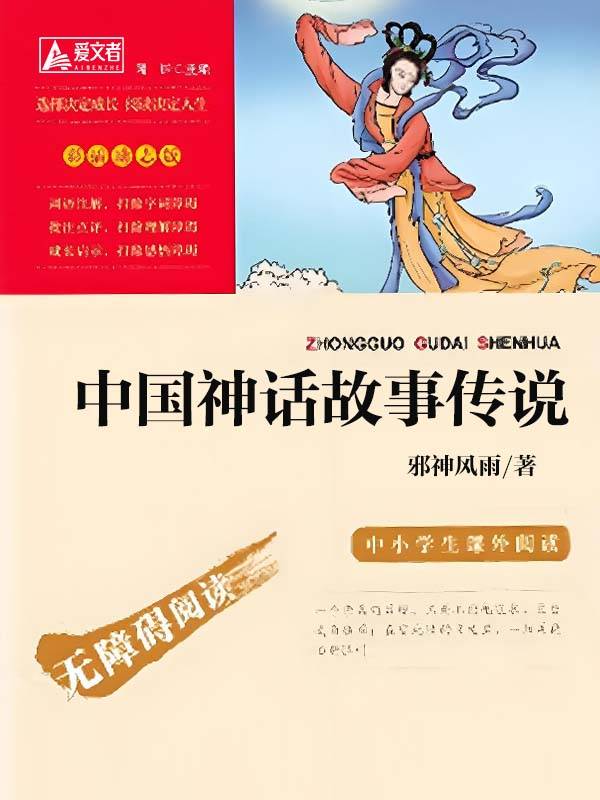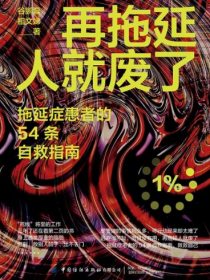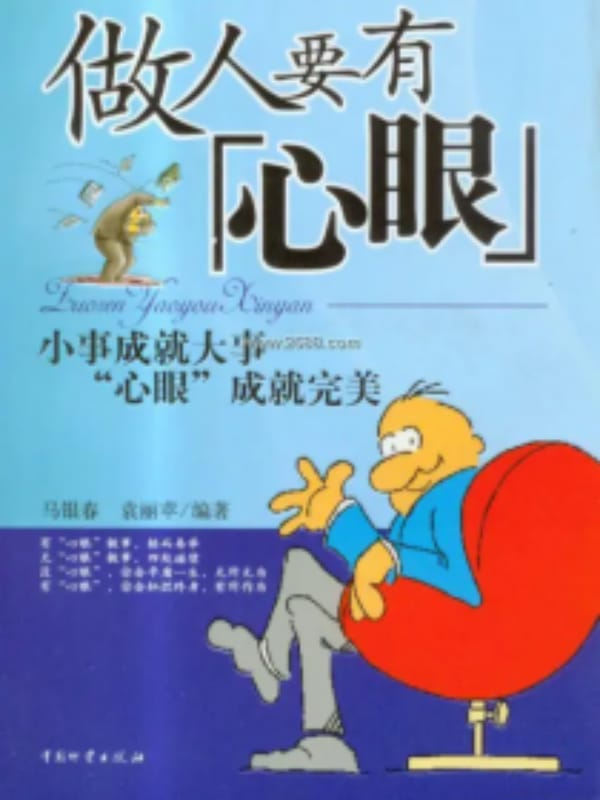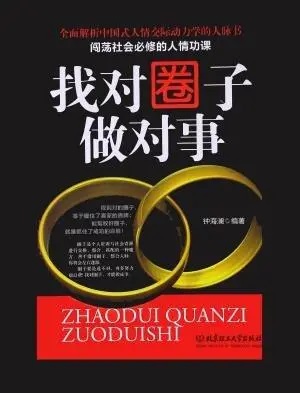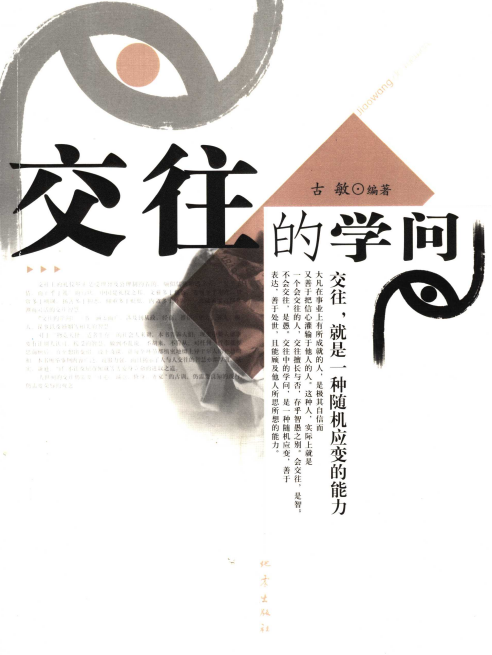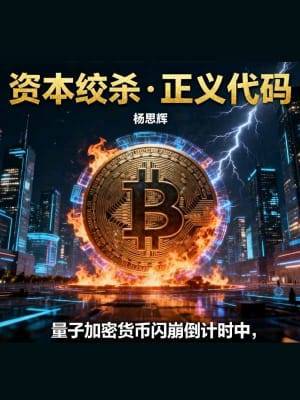目录

加入书架
(二百八十九)出淤泥而不染,濯清涟而不
工作室:北宫伯玉发布作者:北宫伯玉发布时间:2023-01-28
出淤泥而不染,濯清涟而不妖(上)
本篇参考剧情第四十三集
虽然贤者润莲啰啰嗦嗦地说了半天,其实阳光底下也没啥新鲜事,甭管是采盐、挖矿还是织丝绸、织棉布,对于那些有志于从事垄断行业的黑心资本家而言,想要快速实现财富自由,诀窍只有两条,一是官商勾结、二是剥削劳工,仅此而已。而且有一说一,盐井冒水、铜矿坍塌死的那点儿人,也就刚刚够道长运五根梁木进京的,跟毁堤淹田那种大场面比起来,根本就不在一个数量级上,实在不值一提。讲道理,如今这世道,连京官家里都没余粮过年了,去年一场大雪,北京城外冻死数千饿殍,宛平、大兴两县更是十室九空,道长眼皮子底下尚且如此不堪,天高皇帝远的南直隶,又能好到哪里去。借用吕公公的一句话,左右不就是德兴和泰州两地生了民变嘛,无非是一小撮不明真相的群众,受了妖人蛊惑罢了,反正也成不了什么气候,道长他老人家心里装的可是九州万方啊。
大明朝两京一十三省,几无一尺净土,像王用汲口中说的这种,上下勾结、沆瀣一气,颠倒黑白、官逼民反之类的事,简直不要太多,对朝廷而言,能不出事最好,出了事也无所谓,只要地方官能把自己屁股擦干净,朝廷那边也乐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自然不会多管闲事。虽然南直隶生了民变,但朝廷这边也是虱子多了不痒、债多了不愁,按惯例发了一纸公文,然后应付差事似的,随便从都察院派了个六品官过来查案,也就仅此而已了。德兴和泰州的地方官也是运气不好,好死不死都察院派了贤者润莲过来查案,活该他们倒霉,本来只是个“失察”的罪名,让王大人这么一搅合,弄不好真要罢官抄家了。不得不说,经过了几年的历练,王润莲如今也成熟了不少,至少人家知道,哪些人能查,哪些人不能查,王大人好不容易来南京出趟差,临走的时候,怎么也得抓几个地方官,回都察院交差才行,至于那些监井矿的太监,王大人可惹不起,烫手的山芋还是早点甩出去的好。
有一说一,衙门口刚见面的时候,王用汲管谭伦叫“谭大人”;进了签押房,求谭大人密奏皇上,严参太监的时候,便改口称人家“子理兄”了,只能感慨一句,这年头,连贤者润莲也特么学坏了。无论是丝绸作坊,还是盐井、铜矿,看看杨金水便知道了,似这般一等一的肥缺,任上的太监,必定是司礼监那位老祖宗的体己人才行,王用汲竟然撺掇谭伦去主动招惹此等是非,这用心也是忒歹毒了些。须知道,如今司礼监里的那位老祖宗,可不像当初吕芳那般好说话,说是密奏皇上严参,可这种事儿,又怎能瞒地过陈洪的耳目,你王用汲上嘴唇一碰下嘴唇,喊一句“子理兄”,便要人家谭大人去得罪陈公公,你当人家谭子理是海刚峰嘛。谭伦心中一阵冷笑,也不答话,只是黑着个脸,意味深长地瞥了王用汲一眼,站起身不慌不忙地踱了几步,冲着上茶的书办吩咐一声,“你去把门关上,任何事、任何人不要来烦我”,那书办应了声“是”便退了出去。
王用汲见状暗暗叹了口气,随即起身,凑到谭伦面前,无奈地问道,“又有谁打招呼了嘛”,贤者润莲刚才还嚷嚷着说,要“查出一个就抓一个”,此时一个“又”字脱口而出,无意中却是一语道破了天机。谭伦板着面孔故意不去看王用汲,双眼盯着地面,轻叹一声感慨道,“这个案子已经不算什么事了,你也不能在南京待了,明天就得立刻回京师”。讲道理,即使海老爷不上《治安疏》,南直隶的案子也算不得什么大事儿,谭大人又不可能真地去上密折弹劾什么太监,最多也就是牵涉到知府这个层面,而且还有一堆人打招呼,少了他王用汲,这案子审起来,谭伦反而还更方便些。
谭伦之所以急吼吼地要把王用汲赶回北京去,其实就是要跟海老爷彻底划清界限,毕竟海瑞上疏作死之前,唯一有过联系的在职官员,便是眼前这位王用汲同志了,而且当初举荐海瑞的,正是谭伦本人。在如此敏感的时刻,海老爷的两位故人,又齐聚在南京共事,这瓜田李下的,难免会让有心人浮想联翩,谁知道这俩人凑在一起,到底是在查案子,还是在密谋搞串联呢。正所谓爱屋及乌、恨屋也及乌,谭子理此时最担心的便是,道长因为海瑞的事而迁怒自己,毕竟自己身上的嫌疑,一点儿也不比那赵孟静轻,偏偏自己又是裕王的门人,连个做天子门生的机会都没有。海瑞在北京捅破了天,案子又牵涉到了王用汲,谭大人自己都还没摘干净呢,哪还敢让王大人继续留在自己身边惹人怀疑,于是毫不犹豫地逼着贤者润莲,明天一早立马滚蛋。
王用汲闻言,只觉脑中轰地一声巨响,一股强烈的不安感瞬间涌上心头,犹疑了片刻,有些迷茫地望向谭伦,下意识地试探道,“刚峰出事了”。实话实说,海老爷打算批龙鳞的事,去年腊月便有了些许不祥征兆,只可惜最近两个月,海老爷始终引而不发,更是主动切断了跟外界的所有联系,每天都是朝九晚五、两点一线,连那些盯梢的锦衣卫,也渐渐对他放松了警惕。虽说事出反常必有妖,可这世上只有千日做贼,哪有千日防贼的道理,即使明知道海老爷居心叵测、心怀不良,王用汲也拿他没什么办法,凡事论迹不论心,若不是那封横空出世的《治安疏》,估计赵贞吉都要误会海老爷从良了。谭伦又向前踱了几步,转过身漠然地盯着王用汲的背影,淡淡地说道,“是,海刚峰已经被抓了”,王用汲眼中火光一闪而逝,转身面向谭大人,沉默了片刻,方才故意装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模样,脱口而出喊了声,“他上疏了”。
谭伦眼中闪着寒芒,心中暗暗盘算着,自己刚才只是说海刚峰被抓了,又没说海瑞到底犯了什么事儿,隔着几千里远,你王用汲怎么知道,海老爷因为上疏,而不是因为嫖娼被抓的,还特么说自己不是同谋,这下不打自招了吧。其实王用汲也是故意卖了个破绽,想要摸摸谭大人的底,看看这谭子理对海刚峰到底是个什么态度。贤者润莲心里清楚,自己只是个六品官,人微言轻的,回了京城也没啥鸟用,估计连去诏狱探监的资格都不够;人家谭子理却不同,贵为一剩巡抚,身后还站着裕王,虽说是个明哲保身的怂货,但毕竟当初是他举荐的海瑞,哪怕不念旧情,仅仅是为了自保,指不定谭大人就被猪油蒙了心,还真能拉海老爷一把呢。谭伦有些嫌弃地看着王用汲,口气中已是多了一丝疏远,“是,奏疏的抄件,内阁已经急递给我,触目惊心哪”,王用汲则是用满怀期待的眼神望着谭伦,轻声问道,“可否给我一看”。
讲道理,王用汲区区一个六品小官,哪有资格去拜读海老爷的神作,他只知道海刚峰上疏批了龙鳞,却根本不晓得奏疏里到底写了什么,好奇心作祟之下,下意识地想请谭大人给他透个底。正所谓此时彼一时也彼一时也,若是在几年前,俩人还是亲密战友的时候,似这般夜半三更暗室之内,又是天知、地知、你知、我知的事儿,奏疏的抄件看也就看了,说不定,俩人还得坐在一起,好好商量商量接下来该怎么办呢;只可惜时过境迁、物是人非,谭子理依旧是那个腹黑的谭子理,王润莲却再也不是那个善良的王润莲了,这老实人一旦有了心眼儿,可比坏人要难缠多了,谭大人也不得不防一手啊。谭伦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嘴脸,义正辞严地告诫道,“你最好一个字不看,一个字都不知道为好”。开玩笑,在谭大人看来,王润莲这厮事前就知道海刚峰要上疏,这货铁定是那海瑞的同党,如今还想借自己的手,去偷看奏疏的抄件,摆明了就是要拉自己下水。若不是考虑那海刚峰是自己举荐的,裕王又对他赞不绝口,谭大人此时都恨不得立刻把王用汲扔囚车里槛送京师,来自证清白了。
见谭伦拒绝地如此坚决果断,王用汲眼中闪过一抹深深的失望,神色也不由得黯淡了几分,一个劲儿地摇头,自顾自地叹息道,“我现在知道,他为什么怂恿我向都察院讨了这个差使离开北京。我早就应该想到,他这是不想牵连我。太夫人呢,嫂夫人还有身孕呢,她们怎么办?”谭伦幽怨地望着王用汲,心里不禁吐槽了一句,我也不想你王润莲留在这里牵连“我”,只希望明天一早就离开南京,俗话说爹死娘嫁人,各人顾各人,与其这会儿担心海瑞的家人,你王润莲还是多考虑考虑你自己吧,嫂夫人有身孕又如何,那孩子也不是你的,真特么是咸吃萝卜淡操心。“你不要管了,你也管不了了”,谭伦依旧是那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,随口说了句风凉话,话虽然说地有些凉薄,但道理确实是这么个道理。谭大人瞥了眼满脸愤懑的王用汲,也意识到自己刚才失言了,脸颊微微一红,朝旁边挪了几步,坐在椅子上长叹一声,惺惺作态地感慨道,“说到底是我误了他,嘉靖四十年,要不是我力荐他出任淳安知县,他现在已在老家采菊东篱了……也不会惹来这场杀身之祸”。
 添加表情
添加表情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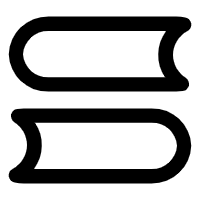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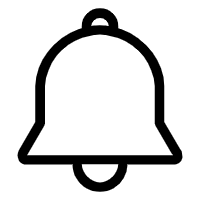 0
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