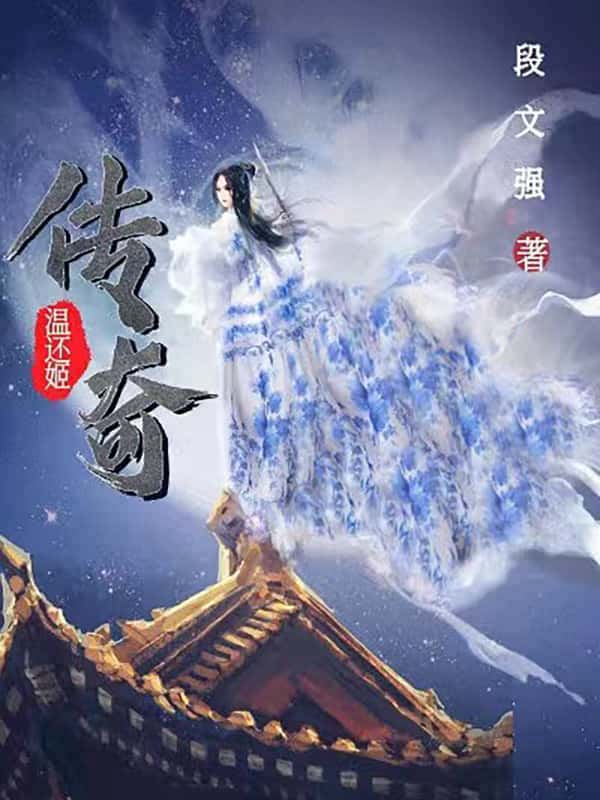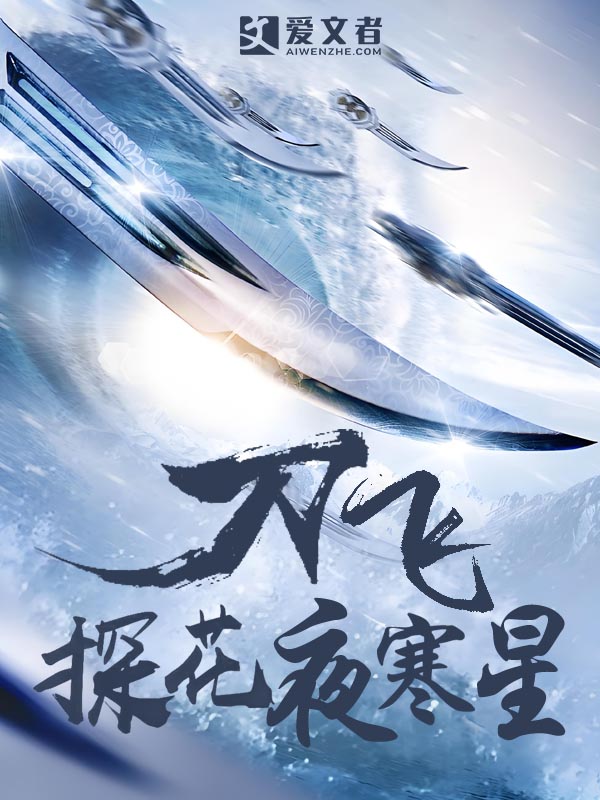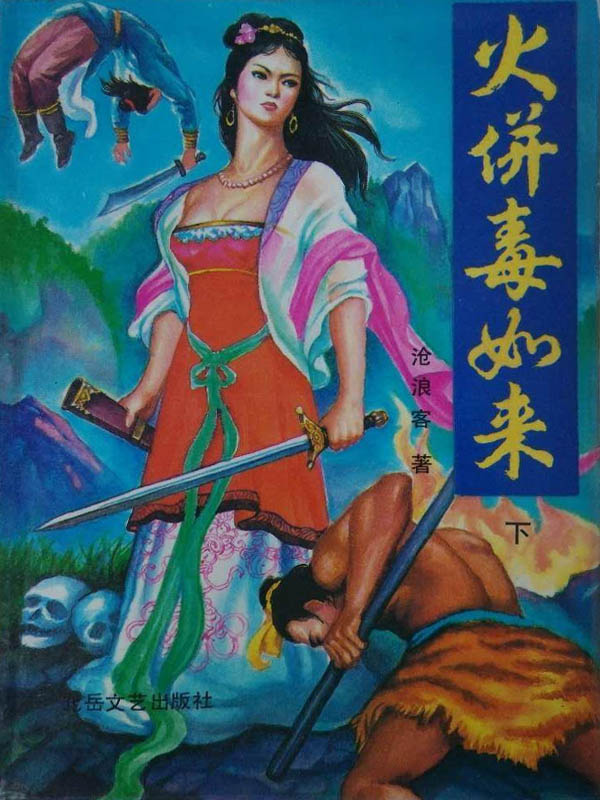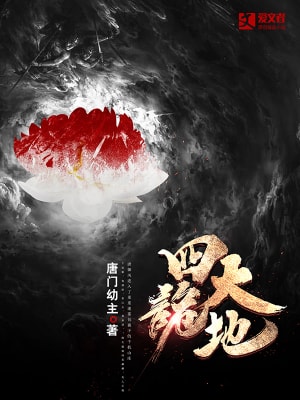目录

加入书架
戏子
工作室:苗疆公子发布作者:苗疆公子发布时间:2025-04-02
扬州城的暮色浸着血。林鹤踩着细密的鼓点旋身,水袖在残阳里甩出半道虹。台下空荡荡的檀木椅映着西天火烧云,像泼了满地的胭脂。
"报——!"小厮撞开朱漆斑驳的园门,"史督师...史督师在城头中箭了!"
柳七的翎子颤了颤。他正在描摹最后一道眉峰,金粉顺着笔尖抖落,在铜镜前碎成星子。"师兄,这《击鼓骂曹》还唱么?"菱花镜里映出他上挑的眼尾,胭脂沿着皱纹裂开细缝。
林鹤的白绸靴碾过满地狼藉。前日班主卷了细软出逃,打翻的脂粉匣子泼出五色斑斓,混着不知谁遗落的翡翠耳珰。"开弓没有回头箭。"他挑起案头那柄木剑,剑穗上缀着的银铃铛叮当作响,"你听。"
远处闷雷滚动。不是春雷,是镶蓝旗的重甲骑兵踏过青石板路。柳七的护甲忽然勒得喉头发紧,他想起清晨在渡口看见的浮尸,泡胀的指尖还勾着半截琵琶弦。
戌时三刻,多铎的马鞭抽裂了东陵戏园的匾额。亲兵举着火把鱼贯而入,铁靴震得戏台簌簌落灰。林鹤正在唱"奸雄休要逞猖狂",忽见柳七的翎子掠过眼前,寒光乍现。
"师兄小心!"柳七的惊呼裹在翎子镖破空声里。林鹤旋身避让,木剑堪堪架住三枚暗器,却在看清镖尾纹样时瞳孔骤缩——那分明是班主私藏的波斯金箔。
镶白旗参领哈鲁台抛来一袋金锭,砸在褪色的织锦地毯上闷响。"二十两。"满语混着汉话,像钝刀刮过青瓷,"唱《四郎探母》。"
柳七的护指抠进雕花栏杆。他看见金锭从鹿皮袋口滚出来,在火把下泛着柔润的光,像极了幼时班主锁在檀木匣里的贡品。"军爷,这《四郎探母》要改徽调皮黄才入味..."他躬身上前,袖中暗藏的蒺藜刺却对准林鹤后心。
林鹤的白绸靴突然挑起案上铜磬。嗡鸣声里木剑破空,将柳七的暗器钉在描金柱上。"师弟何时学了燕山派的蒺藜打穴手?"剑穗银铃叮咚,映着他眼底寒霜,"可是那日翻检班主的密室所得?"
"师兄不也藏着史可法的密信么?"柳七忽然尖笑,金丝戏服在火光里泛着血泽。他袖中甩出九节鞭,鞭梢钢刺直取林鹤咽喉,"扬州城都要化了灰,还守着戏本子当圣旨!"
多铎抚掌大笑。亲兵们跟着哄闹,火把投下的黑影在戏台上张牙舞爪。林鹤翻身跃上悬在梁间的素绸,水袖翻卷处寒星点点——竟是藏了三百六十五根绣花针。柳七的鞭影如毒蛇缠柱,却总被银针击偏三分。
"去年腊月班主暴毙,"林鹤足尖点在绸缎上,宛如凌波仙子,"他房中的孔雀胆..."
柳七瞳孔骤缩,九节鞭陡然转向多铎!这一鞭裹着十年功底,钢刺直取咽喉。却见寒光闪过,哈鲁台的弯刀已斩断鞭梢。柳七踉跄后退,忽然袖中爆开毒烟。
林鹤的白绸倏然垂落,卷住柳七腰身狠狠掼在戏台。描金地砖裂开蛛网纹,柳七咳出血沫,金冠歪斜露出鬓角白发。"你...你早知..."他瞪着林鹤手中密信,火漆印着史可法的官印。
"班主密室有暗格。"林鹤剑指他咽喉,"那封给洪承畴的降书,是你代笔的?"
多铎的掌声惊飞夜枭。火把突然齐齐熄灭,柳七的毒蒺藜在黑暗中暴雨般激射。林鹤闭目听风,木剑划出圆弧,银针与暗器相撞迸出火星。再睁眼时,柳七的金丝戏服已缠住哈鲁台的弯刀,染血的指尖正摸向那袋金锭。
寅时三刻,扬州城破了。林鹤抱着断弦的月琴走出戏园,身后传来梁柱倾塌的轰鸣。柳七最后那声惨叫混着清军哄笑,像极了他们儿时共演的《目连救母》里,地狱恶鬼的嘶吼。
残月照着淮河水,水面漂着胭脂盒与断翎子。林鹤的白绸衣袂掠过血泊,忽然顿住——柳七至死攥着的金锭上,赫然烙着"崇祯通宝"。
淮河渡口的芦苇荡里飘着焦糊味。林鹤的月琴撞在青石上,十三根弦齐刷刷崩断——镶蓝旗的斥候骑兵正举着火把沿河搜捕。他蜷在渔舟残骸后,忽觉掌心刺痛,原是那枚沾着柳七血迹的金锭,正将"崇祯通宝"四字烙进皮肉。
"班主说过..."林鹤盯着掌纹里渗出的血珠,想起那个暴雨夜。老班主醉醺醺指着满箱金箔:"戏子分三等,下等卖艺,中等卖身,上等卖魂。"
芦苇丛忽然簌簌作响。林鹤反手甩出水袖,银针却在看清来人时凝住——是个抱着婴孩的妇人,襁褓上绣着东陵戏班的凤穿牡丹纹。
"班主的相好。"他认出妇人鬓角的金累丝点翠簪,正是柳七去年中秋献给班主的寿礼。那夜柳七唱完《游龙戏凤》,簪子就不见了。
妇人忽然跪倒,额头磕在碎石滩上咚咚作响:"林相公,史督师的副将藏在瓜洲渡..."她掀开襁褓,婴儿掌心攥着半枚虎符,"他们说您有密信渠道。"
林鹤的银针倏然抵住妇人咽喉。月琴裂开的腹腔里,史可法的密信正在泛潮。七天前他扮作货郎混出城时,守备将军往他琴匣塞进这个油布包,说事关南明十万残军存亡。
"柳七的毒蒺藜滋味如何?"妇人忽然轻笑,指尖抚过婴儿脖颈,露出三枚紫黑指痕,"那蠢货到死都以为孔雀胆是我下的。"
火把的爆裂声逼近,林鹤的水袖卷起婴孩。妇人突然暴起,发间金簪射出一道银线——竟是淬了剧毒的琴弦!林鹤旋身避让,月琴残骸却被弦丝切作两半,密信飘飘荡荡落向河面。
镶蓝旗骑兵的狼牙箭破空而至。林鹤踏着芦苇疾退,水袖卷住密信的刹那,箭簇已穿透肩胛。他借着冲力扑进淮河,却见那妇人抱着块浮木漂来,染丹蔻的指甲正抓向自己伤口。
"哈鲁台大人许了我扬州教坊司的位置。"她在浪花里笑得癫狂,金簪上的珍珠被血污黏成赤色,"就像柳七说的,戏台塌了总要找新东家..."
林鹤忽然松开水袖。密信顺流而下,他反手将金锭塞进婴孩襁褓。妇人的尖叫混在波涛声里,镶蓝旗的箭雨笼罩河面时,他看见那枚"崇祯通宝"的金锭在襁褓中泛着冷光,像极了柳七咽气时暴突的眼球。
第一幕:霓裳舞尽山河泪
林鹤的银针撞上琴弦时,迸出的火星照亮了他记忆里的某个清晨。那年他十二岁,柳七的九节鞭第一次缠住他的木剑。班主捏着翡翠烟杆冷笑:"小鹤子使的是《霸王别姬》的剑舞,柳七儿这鞭法...倒像《水浒》里偷鸡的时迁!"
河面的冷雨将回忆浇得透湿。妇人弹出的"商弦"卷着相思蛊袭来,林鹤本能地使出霓裳第七旋"惊鸿照影"。水袖搅动的漩涡中,他恍惚看见初次登台时的自己——十六岁少年将白绸甩成流云,台下柳七捧着金丝戏服候场,眼里映着班主匣子里的夜明珠。
"你还在做虞姬自刎的梦!"妇人的尖叫刺破幻象。她的金簪炸开毒雾,七根琴弦在紫烟里绷成绞索。林鹤翻身踏浪,袖中银针排列成《满江红》的工尺谱——这是史可法亲兵半月前潜入戏园时,蘸着茶水在戏本上画的暗号。
羽弦震颤的刹那,婴孩虎符突然发出埙声般的呜咽。林鹤的孔雀翎堪堪抵住哈鲁台的弯刀,翎毛缝隙间突然闪过柳七最后的眼神:那夜在后台,柳七用染着蔻丹的指甲抠木匣锁眼,金箔划破指尖时也是这般猩红。
"接刀!"哈鲁台忽然改用字正腔圆的官话。林鹤的水袖缠住刀柄时浑身剧震——这招"反手撩云"分明是柳七的成名绝技!当年《林冲夜奔》的戏台上,柳七正是用这式挑飞他头冠上的绒球,惹得满堂喝彩。
妇人的指甲抓裂林鹤肩头时,他嗅到了班主房里的龙涎香。那个暴雨夜,他跪在暴毙的班主榻前,发现孔雀胆药瓶底下压着半张曲谱。柳七提着灯笼推门而入,戏袍下摆沾着淮河渡口的淤泥。
"羽弦勾的是肾水。"林鹤突然开口,银针顺着琴弦震颤的波峰逆流而上。妇人踉跄后退,金簪上的珍珠滚落河面——每颗珠子内里都刻着微型戏文,正是柳七笔迹。
婴孩的啼哭忽然转为《四郎探母》的唱腔。林鹤的瞳孔猛地收缩,这是班主独创的"腹语传音"!他旋即将水袖甩成屏障,三百银针在袖面排成当年密室墙上的《破阵图》。
"你可知这虎符要蘸童血才能显影?"妇人忽然撕开襁褓。林鹤的银针凝在半空,他看见婴儿心口纹着东陵戏班的火焰纹——和柳七锁骨下的刺青一模一样。记忆如潮水倒灌:十二岁那年中元节,柳七被班主按在香案上刺青时,咬碎了含在嘴里的饴糖。
角弦迸发的腐骨散染绿了半边河水。林鹤踏着浮尸跃起,使出了柳七教他的"踏雪寻梅"。这招本用于《游园惊梦》的鬼步,此刻踏在清兵尸首上,竟每一步都溅起带毒的脑浆。妇人狂笑着拨动徵弦,火毒顺着音波灼穿林鹤的袖袍,露出臂上结痂的鞭痕——那是柳七最后一次与他拆招留下的。
当林鹤的银针终于穿透七情锁魂阵的"宫弦"节点时,哈鲁台的弯刀也劈开了金锭。飞溅的碎金中,史可法的血书在晨光里舒展如旗,每行字迹都是班主亲授的"水袖体"。
"原来你早就是史可法的暗桩!"妇人呕着黑血嘶吼。她的金簪寸寸碎裂,露出里面柳七画的扬州布防图——用胭脂混着人血勾勒的线条,正是《长生殿》里鹊桥的走位。
林鹤的白绸缠住婴孩的瞬间,掌心突然传来灼痛。金锭残片上的"崇祯通宝"正在吸食他的鲜血,逐渐显露出班主的遗言:"艺成之日,尔等需择一人祭旗"。他忽然懂了柳七那夜为何盗取孔雀胆——他们本就是班主培养的"阴阳戏傀",一个继承忠魂,一个注定成叛。
哈鲁台的弯刀再次袭来时,林鹤使出了禁忌的第十八旋"羽化登仙"。这招要折寿十年的秘技,需将水袖缠住自己脖颈旋身飞转。银针随血珠激射,在半空拼出《击鼓骂曹》的唱词。妇人被钉在桅杆上的尸体突然睁眼,唱起了柳七最拿手的《夜奔》:"回首西山日又斜,天涯孤客真难度..."
当林鹤抱着婴孩跌进对岸芦苇丛时,怀中的虎符突然开裂。半块玉珏滚落出来,纹路与柳七生前佩戴的玉佩严丝合缝。他颤抖着扯开婴儿襁褓,心口火焰纹下赫然藏着两行小楷:
"崇祯十四年冬,拾于扬州东陵戏园"
冷月从云层后探出,照得河面碎金浮动。林鹤突然发笑,笑声惊起夜枭。他想起自己与柳七并称"淮河双璧"的那些年,一个专攻青衣,一个善演武生。如今才明白,他们不过是班主排的连台本戏里,注定相杀的生旦。
二十年后,南京聚宝门外新开的戏园里。当家武生使完"踏雪寻梅"后,忽然朝台下甩出三枚镀银翎子镖。包厢里的富商咽喉溅血时,看客们惊觉那镖尾纹样,正是崇祯年间扬州东陵戏班独有的金箔牡丹。
更鼓声里,班主模样的黑影从后台闪过,手里把玩着半枚带血的金锭。
 添加表情
添加表情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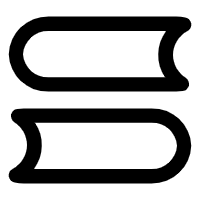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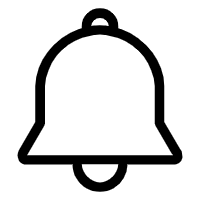 0
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