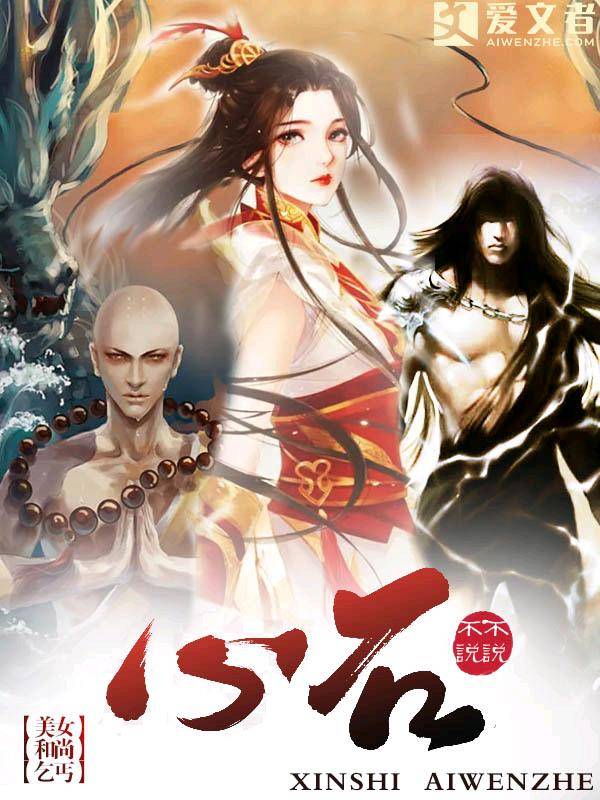目录

加入书架
枭雄
工作室:苗疆公子发布作者:苗疆公子发布时间:2025-05-16
一、雪夜惊变
腊月十六的雪像是天上破了窟窿,沈石攥着镰刀往山坳里钻时,后脖颈的冰碴子已经冻成了铠甲。三天没进一粒米的肚子火烧火燎地疼,他扒开雪堆的手指却不敢停——枯草根底下那点发黑的葛藤,是沈家沟最后能嚼出汁水的活物。
狼嚎声贴着山脊滚过来时,他正把半截草根往怀里塞。五对绿莹莹的光点在雪幕里忽明忽灭,领头的那只独耳灰狼前爪刨着地,冰渣子混着口涎甩在沈石冻裂的麻鞋上。他反手把镰刀横在胸前,刀刃缺了三道口子,是上个月砍柴时从石头上崩的。
"要命的来。"少年喉咙里滚出沙哑的呜咽,后背死死抵住岩壁。头狼扑上来的瞬间,他抡圆了镰刀往斜下方劈,刀刃卡进狼脖子时喷出的血柱烫得他手一抖。腥气激得狼群发了狂,两只半大的狼崽子左右包抄,獠牙撕开他左腿的棉裤,冰碴混着血沫灌进伤口。
沈石摸到块棱角尖锐的石头,反手砸进狼崽子的眼窝。温热的脏器溅上睫毛时,他忽然听见山下传来撕心裂肺的哭喊。那是母亲的声音,混在风里像根生锈的钉子,直直扎进他太阳穴。
雪地上拖出的血痕从村口蜿蜒到冰河,沈石瘸着腿冲到渡口时,正看见地主管家的皂靴碾在母亲手指上。装粮种的粗布口袋裂了口,黍米粒顺着冰面滚进河中央的裂缝。"沈家欠的租子,拿命抵也便宜你们了!"管家抬脚要把人往冰窟窿里踹,母亲突然抱住他的腿,朝着沈石藏身的草垛嘶喊:"跑!往北——"
冰层断裂的脆响淹没了尾音。沈石眼睁睁看着那团灰扑扑的棉袄消失在墨色河水里,管家靴尖上沾着的雪,白得刺眼。
沈石的膝盖砸在冰面上时,黍米粒正顺着冰缝往下沉。管家带着人往村里去了,雪地上零星散落的粮种被靴底碾进泥里,像撒了一地的血痂。他扒着冰窟窿往下看,黑水里浮着母亲散开的发髻,灰白的发丝缠住一株冻僵的水草,晃悠悠地打着旋。
"娘,我给你捡回来。"少年把镰刀咬在嘴里,十指抠住冰面往下探。棉袄吸饱了冰水越来越沉,指尖离那团黑影始终差着三寸。冰层突然开裂的瞬间,后领被人猛地揪住,老猎户陈三的柴刀卡住了他下坠的势头。
"你不要命了!"陈三的破毡帽滴着水,刚才那下猛拽让他的旧伤又渗了血,"周阎王的人还在村里搜粮,听见水响折回来,你们沈家就绝户了!"
沈石喉头动了动,吐不出半个字。他盯着冰窟窿里最后冒上来的气泡,突然抓起镰刀往冰面上砍。刀刃崩飞的碎片擦过脸颊,在颧骨拉开道血口子,融化的雪水混着血滴进冰缝,冻成一条蜿蜒的红线。
陈三把少年拖进芦苇荡时,村里的哭喊声正顺着风飘过来。地主的护院在砸沈家的门板,缺了角的石磨被推倒,碾碎窗台下晒着的草药——那是母亲去年夏天采的紫珠草,说好了开春拿到镇上换盐。
"北坡山神庙。"老猎户往沈石怀里塞了块烤硬的芋头,兽皮坎肩的膻味混着话一起喷在他脸上,"躲过今夜,顺着野枣树往北走三十里,别回头。"
沈石没接芋头。他褪下左脚的草鞋塞进冰窟窿,又抓了把带血的雪按在眉心。这是沈家沟祖辈传下来的送葬法子,活人衣冠沉水,魂灵就找得到归家的路。冰层下的黑影渐渐模糊时,他对着河心磕了三个响头,前额在冰面上印出朵红梅。
山神庙的瓦当缺了半边,月光像把豁口的刀插在供桌上。沈石蜷在神像后头数伤口,左腿被狼咬的地方肿得发亮,手指头早冻得没了知觉。供桌底下有堆发霉的稻草,扒开竟露出半角靛蓝封皮——是本被老鼠啃烂的旧书,封面上"沧浪"二字只剩个"氵"旁。
破庙外忽然传来马蹄声。沈石把书塞进怀里,贴着墙缝往外看。周阎王骑着青骢马立在坡下,护院举的火把照见他镶银的马鞭,鞭梢挂着串铜铃,正是母亲当年陪嫁的压箱物件。
"小畜生肯定躲在这一带。"周阎王的声音像钝刀刮骨,"找不着活的,死的也行。"
马蹄声逼近山门时,沈石摸到了神像底座下的暗格。三枚生锈的铁蒺藜滚出来,尖刺上泛着诡异的幽蓝——是淬过毒的。他想起陈三说过,十年前有个受伤的剑客在这庙里住过半月。
火把的光晕染红门缝时,沈石已经缩进神像腹中的夹层。蜘蛛网糊在脸上又痒又疼,怀里的旧书硌着肋骨,他闻到自己的血味混着霉味在黑暗里发酵。护院的刀尖划过供桌,木屑簌簌落在夹层入口,有只蝎子顺着他的脚踝往上爬。
"这有血!"护院突然吼了一嗓子。沈石看见自己留在稻草上的血渍正被火把烤得发黑,周阎王的马鞭卷起那本《沧浪剑诀》的封皮,火星子溅在靛蓝布面上烧出个窟窿。
夹层里的蝎子尾针扎进小腿时,沈石死死咬住衣袖。疼痛像团火从脚底烧上来,眼前忽地闪过母亲坠河时扬起的衣袖——也是这般带着火星的靛蓝色。神像突然震动起来,护院在推搡雕像找暗门,夹层缝隙里漏进的冷风卷着雪花,把他睫毛冻成了冰帘。
"轰"的一声,山门被狂风撞开。积雪压垮了半朽的横梁,瓦片雨点般砸在周阎王马前。青骢马惊得人立而起,护院们慌忙去拽缰绳。沈石在剧烈的震动中抠住神像内壁,指尖突然触到凹凸的刻痕——是字,倒着刻的《沧浪剑诀》后六式。
马蹄声渐远时,沈石的牙已经咬穿了衣袖。蝎毒让他视线模糊,但刻在神像内壁的剑招反而清晰起来。那些倒悬的笔画在月光下扭曲游动,恍惚间竟与母亲生前纺线的动作重合。他颤抖着摸出铁蒺藜,用尖刺在掌心划出剑路走向,血珠顺着掌纹晕开,像幅诡异的星图。
破晓时分,沈石滚出夹层。右腿彻底没了知觉,他抓着半截桃木剑——那是神像手里的法器——当拐杖往北挪。怀里的残谱被血黏在胸口,风卷着雪片灌进领口,烫得像是周阎王马鞭上的火星子。
三十里外的野枣树挂着霜,树皮上刻着道新鲜的剑痕。沈石瘫在树根下嚼树皮时,听见官道上传来驼铃响。镇远镖局的青龙旗在风雪里猎猎作响,押镖的趟子手正在骂天:"这鬼天气,马都冻得打摆子!"
沈石把铁蒺藜藏进袖口,用最后的气力撞向镖车。枣木剑脱手的瞬间,他听见自己嘶哑的喊声:"我会饮马!给口吃的就行!"
二、剑决残章
镖车碾过结冰的辙印时,沈石蜷在装草料的麻袋堆里发抖。铁蒺藜的毒让右腿肿得像发面馒头,每颠簸一下都似有钢针顺着骨髓往心口钻。他死死咬住从神像腹中撕下的《沧浪剑诀》残页,靛蓝布帛上的墨字被血浸得模糊,倒像是母亲生前绣的蜡梅纹。
"马厩缺个夜班添料的,管饭。"镖头王胡子捏着鼻子打量这瘸腿少年。沈石扑向马槽边的泔水桶时,余光瞥见院角武师晨练的剑光——那招"白虹贯日"的起手式,竟与残谱第三页的"逆浪式"有七分相似。
当夜霜重,沈石拖着伤腿往料草里掺豆粕。马厩挨着西厢房,纸窗上映着总镖头林镇远指点独子练剑的身影。少年郎的剑穗是上好的湖丝,挥动时带起的风声让沈石想起周阎王的银鞭。他抓起搅料的木叉,就着月光比划窗上的剪影,叉尖在泥地上勾出歪扭的剑路。
腊月廿三祭灶夜,镖局上下喝羊肉汤。沈石缩在后厨柴堆旁啃冷馍,忽然听见前院炸开喝彩声——林镇远正演示镇门绝学"伏虎十三式"。他借着添柴的由头蹭到廊柱后,看那柄青钢剑如何劈、挑、缠、绞,剑锋过处,冻硬的沙袋裂作八瓣。
当夜马厩格外冷,沈石用草料在泥地上复刻剑招轨迹。缺了左角的残谱铺在膝头,他惊觉林镇远收剑时的回旋步,竟能补全剑诀第七式缺失的"叠浪"变化。兴奋之下抓起搅料叉演练,叉柄"咔嚓"折断在石槽上,惊得马匹嘶鸣。
"小瘸子半夜作什么妖!"值夜的趟子手拎着灯笼过来踹门。沈石滚进草堆装睡,断柄却从袖口滑落,锋利的木茬上还沾着未干的泥印——正是伏虎剑法的起手式。
灯笼光晕里,趟子手的影子爬上墙。沈石摸向怀中毒蒺藜的瞬间,马厩外突然传来重物坠地声。"有贼!"前院炸开呼喝,趟子手骂咧咧地提棍冲出去。沈石扒着墙缝瞧见五个黑衣人正与镖师缠斗,领头的使一对峨眉刺,招招直奔林镇远咽喉。
淬毒铁蒺藜在掌心硌出血印。沈石鬼使神差地摸近战圈,趁乱将毒蒺藜甩向峨眉刺的锁链关节。黑衣人手腕一滞,林镇远的剑锋已穿透其肩胛。混战中,沈石佯装受惊抱住另一贼人左腿,袖中铁蒺藜顺势扎进对方脚踝。
血战止息时,沈石缩在墙角数伤口——左臂被流矢划破,换来林镇远深深一瞥。总镖头拾起染毒的峨眉刺,突然问:"瘸子,可认得周家庄的徽记?"
沈石盯着刺柄上鎏金的"周"字,喉头泛起冰窟窿的腥气。他指向马槽边惊惶刨地的青骢马:"这畜生眼熟,像是周阎王上月新得的坐骑。"
林镇远抚剑的手顿了顿。次日马厩角落多了卷旧被褥,沈石在褥脚摸到枚生锈的镖师铁牌——正面刻"镇远",背面是道新划的剑痕,与山神庙残谱的起手势分毫不差。
林镇远掷来的铁牌在掌心发烫。沈石蜷在马厩草垛里,就着月光摩挲铁牌背面的剑痕——那笔锋走势与山神庙残谱如出一辙,却在收尾处多出半分圆融,像是江潮撞上礁石后回旋的浪沫。他蘸着马尿在泥地上勾画,木棍划到第七个回环时突然顿住:若将伏虎拳的腰马发力融进剑诀第三式,或许能补全缺失的"叠浪"变化。
腊月廿八扫尘日,镖局上下忙着悬桃符。沈石拖着瘸腿清扫演武场积雪,眼角却粘在场中练剑的林家少爷身上。少年正习练"伏虎十三式"最后一招"虎踞龙盘",剑尖挑起时腕力虚浮,生生将杀招舞成了花架子。
"看够了吗?"林家少爷的剑鞘突然抵住沈石喉头。围观镖师哄笑中,少年腕上玉镯叮当——那是周阎王去年寿宴上见过的和田青玉镯。
沈石垂眼盯着剑鞘纹路:"少爷的剑穗该换了。"他指向被雪压弯的槐树枝,"湖丝吸了潮气发沉,不如换马尾鬃。"趁对方愣神,他佯装踉跄扑向兵器架,袖中铁蒺藜悄然挑断扎绳。十数柄木剑轰然坠地,林家少爷的锦靴正踩在沈石刻意摆放的剑柄上,剑身弹起的弧度恰似残谱中的"挑月式"。
当夜马厩来了不速之客。沈石被冰水泼醒时,三个护院模样的汉子堵在门前,为首的脸生黑痣,正是周阎王贴身侍卫。"小畜生倒是会躲。"黑痣汉的九节鞭缠住沈石伤腿,"老爷说了,你娘的尸首还在冰窟窿里泡着,正好捉你下去作伴。"
马匹突然惊嘶。沈石借势滚向料槽,扬手将毒蒺藜甩进马群。受惊的马匹撞开护院,他趁机攀上横梁,怀中的铁牌不慎滑落。黑痣汉拾起铁牌冷笑:"镇远镖局私藏逃奴,明日便让林镇远跪着交人!"
五更天,沈石跪在林镇远书房。总镖头抚摸着铁牌上的剑痕,忽然将茶盏砸向火盆:"十年前沧浪客重伤垂危,我赠他铁牌求医,他却死在半途。"炭火爆开的火星中,剑鞘挑起沈石下颌,"你这手偷师的本事,倒有他七分神韵。"
院外传来急促马蹄声。周阎王的青骢马踏破晨雾,马背上捆着个血人——正是老猎户陈三。"林总镖头好胆色!"周阎王的银鞭卷起陈三断指,"连我家的逃奴都敢窝藏。"
沈石指甲抠进掌心旧伤。他看见林镇远握剑的手背青筋暴起,更看见陈三耷拉的脑袋突然抬起——老人浑浊的右眼朝他眨了眨,那是猎户诱捕野猪时的暗号。
"镖局确有沈姓马夫。"林镇远突然开口,"不过三日前已被逐出..."话音未落,陈三猛地挣断绳索,独臂袖箭直射周阎王面门!混乱中沈石撞翻火盆,炭火引燃梁上垂落的桃符,浓烟裹着他窜向西墙狗洞。
"追!"周阎王的咆哮混着马蹄声碾过耳膜。沈石在巷口撞见个戴斗笠的货郎,对方袖中滑出柄短剑——剑格刻着浪花纹,与残谱最后一页的印记严丝合缝。
"沧浪不绝。"货郎低语如风过耳。沈石反手扣住对方脉门,触到虎口厚茧的瞬间,忽然明白这是山神庙剑客的传人。追兵将至,货郎劈手夺过铁牌塞进鱼篓:"明日午时三刻,漕帮码头见。"
沈石折返镖局时,大火已吞没半个马厩。林家少爷的断剑插在焦土中,剑穗烧剩的半截湖丝上,沾着星点靛蓝布屑——正是《沧浪剑诀》残页的色泽。他跪在滚烫的瓦砾间扒拉,指尖触到个铁盒:盒内躺着柄生锈的软剑,剑身缠着张血书,落款是十年前的字迹——
"沧浪未尽,赠有缘人。"
三、初露锋芒
软剑缠在腰间的第三夜,沈石摸清了镖局巡夜的规律。寅时三刻,西北角墙根下会有半盏茶的空隙——足够他翻进藏书阁顶层的暗室。月光从鳞瓦缝漏下时,他正用舌尖舔开《伏虎拳谱》的锁扣,却嗅到一股熟悉的腥甜味。
"小友夜访,不尝尝老夫的云雾茶么?" 林镇远的声音在梁上响起,烛火骤亮。沈石的袖中软剑尚未出鞘,已被一枚铁莲子钉入墙缝。总镖头抚着茶盏沿口的裂痕——那是十年前沧浪客留下的剑痕。
"沧浪剑讲究逆势而行,你却用来钻狗洞。" 林镇远指尖蘸茶在案上勾画,水痕竟与软剑血书上的招式暗合,"当年沧浪客重伤垂死,托我保管此剑,等的便是能解'倒悬七星局'之人。"
沈石瞳孔骤缩。案上水痕渐次干涸,最后七滴茶水悬而不落,恰似北斗倒转。他鬼使神差地并指戳向天权位,指尖触到冰凉剑锋——林镇远的青钢剑不知何时已抵住喉头。
"伏虎十三式的破绽在'虎啸山林'变'虎踞龙盘'的转关。" 剑尖忽而游走,在沈石胸前画出道弧线,"若以沧浪第四式'漩流'切入,可破其七寸。"
五更梆子响时,沈石揣着半湿的拳谱回到马厩。草料堆里埋着昨夜偷藏的七枚铜钱,他用软剑挑着铜钱演练剑招。第三枚铜钱弹起时,窗外忽有黑影掠过——是周阎王的探子,靴底沾着城南胭脂铺特有的朱砂泥。
腊月三十祭祖日,镖局大开宴席。沈石被支去后厨剥冻鱼,冰碴子混着鱼血在指缝凝结。前院忽然炸开喝彩,林家少爷正与金陵来的剑客比试。沈石借着送鱼脍蹭到廊下,见那剑客的招式诡谲阴柔,竟与周阎王护院的峨眉刺路数同出一脉。
"看镖!" 剑客突然袖中寒光乍现。林家少爷慌忙格挡时,沈石手中鱼刀脱手飞出——刀背撞偏毒镖,刀刃却削断了剑客的束发带。青丝散落的瞬间,沈石看清对方耳后黥着的黑蝎刺青,正是周家庄死士的标记。
宴席大乱。林镇远拂袖而起时,沈石已缩回灶台后。他摩挲着软剑吞口处的浪花纹,突然明白这场刺杀是冲着自己而来——那剑客袖中暗藏的,分明是山神庙里同款的淬毒铁蒺藜。
子夜守岁时,沈石蹲在马厩顶棚嚼冷炊饼。漕帮货郎的暗号从墙外传来,三长两短的鹧鸪啼。他摸出铁牌在瓦片上轻叩,却听见身后传来衣袂破空声。
"沧浪传人就这点警觉?" 林家少爷的剑锋挑开他衣襟,露出内衬的靛蓝残谱,"爹说你天资过人,我倒要看看..." 话音未落,软剑已如毒蛇吐信缠上其手腕。沈石下意识使出林镇远所授的破招之法,剑尖划过对方玉镯,竟劈出星点火光。
镯裂的脆响惊动巡夜人。沈石翻墙逃窜时,怀中铁牌不慎遗落。货郎在巷口拽住他手腕:"漕帮的船等在西渡口,再迟就..."
"沧浪客当年为何重伤?" 沈石突然发问。货郎袖中短剑一顿,剑柄暗格弹出一粒蜡丸——丸中血书只八字:"漕运图,山神庙,速取。"
正月十五闹花灯那夜,沈石重返山神庙。断梁上垂下的蛛网结了冰凌,神像腹中暗格却多了方鎏金匣。匣开瞬间,机关弩箭贴面而过,钉入墙面的箭簇组成幅微缩漕运图——江河支脉交汇处,正是周阎王新购的茶山。
返程途中,沈石在官道茶棚听见说书人拍醒木:"要说那沧浪客之死,全因窥破漕盐两帮的私运勾当..." 茶碗突然炸裂,说书人喉头插着枚铁蒺藜。周家庄护院从四面合围,领头的手持双刺,正是除夕夜的黑蝎剑客。
软剑卷起茶棚布幡时,沈石瞥见林镇远的白马拴在五丈外的柳树下。他故意卖个破绽,肩头挨了一刺后撞向马腹。白马惊嘶着冲向周家庄护院,鞍袋里滚落的信笺上,赫然是林镇远与漕帮往来的密文。
"沧浪传人不过如此。" 黑蝎剑客的刺尖抵住沈石心口。千钧一发之际,货郎的鱼叉破空而来,叉柄缠着的正是沈石遗落的铁牌。牌面"镇远"二字在月光下泛着血光,反面剑痕突然崩裂,露出内藏的薄刃——竟是一柄钥匙的形状。
"走!" 货郎掷出烟雾弹的刹那,沈石看清他颈后黥着的浪花纹——与软剑吞口处的纹样分毫不差。两人遁入暗河时,追兵的惨叫被水声淹没。货郎扒开胸前皮甲,露出道横贯心口的旧疤:"这伤拜周阎王所赐,沧浪客是为救我而死。"
沈石握紧漕运图的手背青筋暴起。暗河尽头的石壁上,倒悬的七星用朱砂描红,最大那颗天枢星的位置,正对应周家庄茶山下的秘密水道。货郎的鱼叉重重顿地:"沧浪不绝,该清账了。"
柴刀劈进第七柄钢刀的瞬间,沈石听见自己肋骨断裂的脆响。血沫从牙缝里溢出来,混着雨水糊住视线,他却在笑——劫匪头目刀柄上缠着的靛蓝布条,正是周阎王家丁特有的松江细布。
三日前镇远镖局接了趟暗镖,红木匣子送到八十里外的青石镇。林镇远点人时,沈石正蹲在马槽边给青骢马钉掌。铁锤砸偏的声响惊动了总镖头,也惊落了马鞍下藏着的密信——信笺火漆上印着半枚浪花纹,与漕帮货郎的短剑纹路严丝合扣。
"瘸子跟着去。"林镇远的剑鞘突然压住沈石肩头,"你识得山路。"
此刻山道旁的乱葬岗,七个蒙面人围成的杀阵正在收拢。沈石背靠残碑,左手攥着柴刀,右手悄悄摸向腰间软剑——剑身裹着层马粪纸,是今晨从茅房顶梁上撕下来的防水纸。雨水冲刷下,纸浆化开的腥臭反倒盖住了剑锋的寒光。
"小子,匣子留下,赏你全尸。"劫匪头目的刀尖挑向沈石怀中木匣,刃口泛着诡异的青紫色。沈石佯装踉跄,柴刀脱手的刹那,软剑如毒蛇出洞卷住对方手腕。这一式"逆浪回潮"本该断其筋脉,却因力道不足只削下半片衣袖——靛蓝布料下露出黑蝎刺青,正是除夕夜刺客的同伙。
七柄钢刀同时劈下时,沈石突然想起林镇远那夜在案上画的水痕。他踩着倒伏的墓碑腾空,软剑在雨幕中划出七道弧光,每道弧线都精准穿过刀光的间隙。金石相撞的铮鸣里,柴刀不知何时又回到手中,刀刃卡进第三人的刀背豁口,借着对方收刀的力道反劈向第四人面门。
"沧浪剑!"劫匪头目突然暴喝,刀势陡变阴柔。沈石瞳孔骤缩——这招"灵蛇吐信"的路数,竟与山神庙暗格里刻的第九式互为克制。软剑缠上钢刀的瞬间,他故意卖个破绽,肩头硬挨一记刀背重击,左手却将柴刀掷向五丈外的老槐树。
"砰"的一声,树冠惊起群鸦。藏身枝叶间的第八个弓手跌落尘埃,喉头插着把淬毒铁蒺藜——正是沈石从马厩梁上摸来的存货。劫匪阵型大乱的刹那,软剑贴着雨线刺入头目膻中穴,剑锋挑起的衣襟内袋里,滑出半块鎏金令牌,刻着"周记茶山"四字。
林镇远策马赶到时,沈石正用衣摆擦拭软剑。七柄断刀插在泥地里,摆成北斗七星的形状,天枢位正对青石镇方向。总镖头的马鞭突然卷住他手腕:"这招'七星断刃',谁教你的?"
"昨夜看少爷练剑,北斗星正好落在马槽里。"沈石指向地上水洼,水面倒映的云层裂隙恰似剑路走向。林镇远俯身细看断刃切口,瞳孔猛地收缩——刀身断面上的螺旋纹,与十年前沧浪客留下的剑痕一模一样。
回程路上,沈石在颠簸的镖车里拆开红木匣。层层油纸下裹着的不是金银,而是半块染血的漕帮令牌,断口处能拼出个"九"字。令牌背面用蝇头小楷写着:二月初七,龙抬头,茶山煮雪。
当夜马厩来了位不速之客。沈石被浓烟呛醒时,货郎正用鱼叉挑着他的被褥,火星子在靛蓝残谱上烧出个"周"字。"漕帮的船搁浅了。"货郎甩来件蓑衣,"林镇远在查剑痕,你只剩一夜时间。"
子时三刻,沈石摸进镖局祠堂。供桌上摆着的断刀在月光下泛青,刀身映出房梁暗格的黑影。他学着林镇远那夜的手法,将软剑刺入第三块方砖缝隙——机关转动的闷响里,暗格滑出本泛黄的名册,最后一页记着十年前某笔暗镖:
"甲字三号镖,沧浪客押送,经周家庄茶山遇伏,失漕运图半卷,赔付白银千两。"
祠堂外忽然传来脚步声。沈石急将名册塞回时,袖口被铁莲花机关勾住。林镇远的剑锋破窗而入,挑飞的不仅是半截衣袖,还有他藏在臂缚里的淬毒铁蒺藜。
"果然是你。"总镖头的剑尖指向沈石心口,却在他怀中掉出的靛蓝残谱上顿了顿,"沧浪客的剑谱怎会在..."
瓦顶突然炸裂,周家庄死士的弩箭如雨落下。沈石翻滚间撞翻长明灯,火油泼洒处,名册燃起幽蓝火焰。林镇远挥剑格挡时,瞥见烧焦的纸页上"漕运图"三字,手腕不觉一滞。
"镖局东墙狗洞通暗河!"沈石撞开林镇远,肩头替其挡下一支毒箭。软剑缠住房梁垂落的经幡借力荡出,落地时正踩在货郎备好的滑竿上。暗河水流吞没追兵的咒骂时,他摸到滑竿夹层里的密信,血书写着:
"明日茶山,沧浪不绝。"
四、孤身上路
暗河出口的冰棱倒悬如剑,沈石攥着密信的手指已冻得发青。货郎的鱼叉突然横在他颈前,叉尖挑开浸血的衣领——昨夜中的毒箭伤口泛着黑紫,腐肉里嵌着半片碎玉,正是林家少爷被劈裂的镯子残片。
"沧浪客也中过这种毒。"货郎撕开胸前皮甲,心口旧疤蜿蜒如蜈蚣,"周阎王在箭簇上喂的是冰蚕蛊,遇热则毒发。"
沈石扯下束发的草绳扎紧臂膀,软剑在冰面划出火星。当第一缕天光照进暗河时,他望见茶山脚下连营十里的周家商旗,旗面绣的黑蝎在晨风中张牙舞爪。货郎的鱼叉在地上画出三道沟壑:"漕帮兄弟扮作运炭工混进去了三批,折了两批。"
茶山石阶上的积雪掺着煤灰,踩上去咯吱作响。沈石背着炭篓混在挑夫队里,篓底藏着软剑。巡山护院的鞭子抽在脊梁上时,他瞥见半山腰的窑洞冒着青烟——那烟色发蓝,是炼铁才有的焰色。
"新来的,往三号窑!"监工踹翻他的炭篓。沈石弯腰拾炭时,指尖触到地缝渗出的温水——这根本不是茶山,地下藏着温泉暗河!
窑洞深处热浪扑面,二十座铁砧正锻打刀剑。沈石摸到熔炉后的通风口,铁水映出墙上的水道图——周家庄竟将山腹挖空,引暗河驱动水排风箱。淬火池里沉着的剑胚纹路奇特,正是倭寇惯用的逆刃刀。
"看够了吗?"身后突然响起铁链绞动声。八个赤膊大汉封住退路,熔炉暗门里转出个戴青铜面具的人,手中倭刀挑着块带血头皮——是失踪的漕帮暗桩。
沈石甩出炭篓,燃烧的炭块在雾气中炸开红光。软剑卷住铁砧旁的水槽铁链,借力荡向通风口。面具人的倭刀斩断铁链时,淬火池突然沸腾——货郎带人掀翻了地下河闸门!
"走水!"混乱中沈石撞见个熟悉身影。林镇远竟扮作铁匠混在人群里,铁锤砸向他肩头的瞬间,却将个油纸包塞进他衣襟。纸包里是半张漕运图,墨迹未干处标注着"山神庙"三字。
茶山爆炸声响起时,沈石已在密林深处。货郎的右臂齐肩而断,血浸透的布包里裹着块硫磺矿石。"周阎王在炼火器..."他咽气前死死抠住沈石手腕,"山神庙...碑文..."
当夜大雪封山,沈石重返山神庙。断碑上的铭文被雪水泡涨,刮去青苔后显出幅海防图——倭寇登陆的标记点,正是周家庄承包的渔港。供桌下的鼠洞里有具白骨,指骨缠着褪色的靛蓝布条,怀中铁匣锁着另半张漕运图。
卯时三刻,镇远镖局的丧钟惊起寒鸦。沈石跪在林镇远灵堂前,看着棺木里焦黑的尸首——总镖头心口插着柄浪纹短剑,正是货郎的兵器。林家少爷的剑鞘突然压住他后颈:"爹临死前说,沧浪剑该饮血了。"
停灵第七日,周阎王送来鎏金请柬。沈石捧着灵位踏进周府时,满堂宾客正在赌新到的倭国歌姬。酒过三巡,戏台上突然喷出硫磺烟——火器炸响的刹那,软剑已缠住周阎王的脖颈。
"当年冰窟窿的水,可还冷?"沈石剑尖挑开对方貂裘,露出胸口的黑蝎刺青。周阎王狞笑着咳出血沫:"你娘...在水闸..."
青骢马踏破冰河时,沈石看见了终生难忘的景象。母亲的面容竟完好如生,冰层将她定格在仰头呼救的瞬间,怀中紧搂的粮袋里,藏着一枚刻浪纹的铜钥匙——正是漕运图标注的"九宫水闸"总钥。
正月廿八,沧浪盟黑旗插上周家庄主楼。沈石站在檐角洒落混着硫磺的粮种,火光照亮江岸八百艘战船。货郎的鱼叉化作盟主令箭,林家少爷捧着断剑跪呈兵符,江风卷着血腥气灌进他大氅时,对岸忽然传来倭寇的螺号声。
海平线上,三十艘朱印船正扯起风帆。
朱印船的鬼头旗撞上沧浪盟黑旗时,沈石正将铜钥匙插进九宫水闸的龙首锁孔。江风卷着硫磺粉扑在脸上,他想起茶山熔炉里翻滚的铁水——周阎王至死都在狂笑的秘密,此刻正在锁芯中震颤。
"转舵!满帆!"倭寇船头的独眼大将嘶吼着挥动太刀,三十艘战船呈雁翎阵直扑江口。沈石却盯着水面漂浮的黍米粒——那是他故意撒在闸口的粮种,此刻正顺着暗流聚成一道金线。
钥匙拧到第九转时,江底传来闷雷般的轰鸣。林家少爷率领的死士突然从倭船底舱破水而出,他们背上绑着的硫磺筒炸开冲天火光——正是沈石三日前命人混进周家庄运炭船的"炭芯雷"。
"沧浪盟主!"独眼倭将的船头撞角已逼近主舰三丈。沈石解下大氅抛入江中,靛蓝布料展开的刹那,九宫水闸轰然洞开。积蓄十年的暗河怒涛如巨龙翻身,裹挟着沈石提前沉入江心的铁刺木桩,将倭寇战阵冲成两截。
倭将的太刀劈至面门时,沈石手中无剑。他踏着倒卷的浪头跃起,指尖夹着的半粒粮种精准弹入对方独目——这是母亲坠江时攥着的黍米,在冰层里冻了十五年,硬如铁弹。
"这是沈家沟的租子。"沈石踩住倭将咽喉,软剑从浪涛中卷起柄逆刃刀,"连本带利。"刀光闪过,三十颗倭寇头颅随粮种沉入江底,血水染红的江面上,漂起张残破的靛蓝襁褓——正是山神庙白骨怀中的婴儿布。
捷报传回临安城那日,沈石独自跪在山神庙残碑前。货郎的断臂埋进碑下,林家少爷的断剑插在坟头。他烧尽半本《沧浪剑诀》,灰烬里却显出几行隐文——真正的第九式"浪淘沙",需以断刃为引,逆运经脉。
"盟主!漕帮八堂主反了!"传令兵的血溅上残碑时,沈石正用软剑雕刻新碑文。剑锋划过"周阎王"三字,他忽然轻笑:"备船,运粮。"
深夜的沧浪盟地牢,沈石提着盏鱼油灯走过七十二间囚室。八堂主的家眷缩在角落,他蹲下身给孩童分发麦芽糖:"三日后江水涨潮,给你们父兄收尸。"转身时故意遗落块靛蓝碎布——正是母亲棉袄内衬的布料,浸过七日断肠散。
卯时江雾最浓时,八百艘粮船列阵出港。沈石立在船头剥着烤芋头,热气模糊了面容。当叛军舰船进入射程,他突然挥旗令粮船两翼散开——舱内根本不是稻谷,而是三千弓弩手与满舱火油。
"盟主!江上有浮尸!"亲信惊呼。沈石却将芋头抛入江中,看着那些顺流而下的"尸首"突然睁眼——是中毒假死的八堂主,他们脖颈系着浸油麻绳,正随暗流漂向叛军旗舰。
火矢破空时,沈石在冲天火光中摊开漕运图。燃烧的图纸显出血色纹路,竟是张倭国海防图——这才是沧浪客用命守护的秘密。他割开手腕将血涂在图中孤岛上:"该清账了。"
三日后,沧浪盟主舰撞沉最后一艘叛船时,沈石在舱内见到了林家少爷。少年握着他父亲的金刚杵,杵尖抵着自己心口:"你早知道我是周阎王的种。"
"但你娘是沈家沟的采桑女。"沈石扔过个陶罐,罐里蚕茧正吐出靛蓝丝线,"她死前求我,给你留条生路。"
惊蛰雷响时,沧浪盟黑旗插遍三十六水寨。沈石却消失于庆功宴,只在盟主座上留了袋黍米种。有人说见他孤舟出海,也有人说他在沈家沟废墟上搭了间草庐。
直到次年开春,北上的运粮船队在黄河渡口见个跛脚农夫。那人正教孩童在冻土里播粮种,腰间软剑缠着束金黄的麦穗,穗尖上沾着未干的海盐。
江风起时,九宫水闸下的暗格里,染血的沧浪剑诀终卷缓缓展开。末页写着行小楷:
"所谓枭雄,不过是护得住一粒种子的男人。"
 添加表情
添加表情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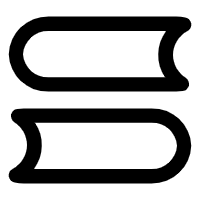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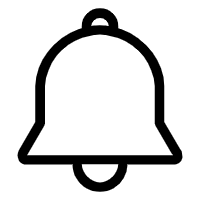 0
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