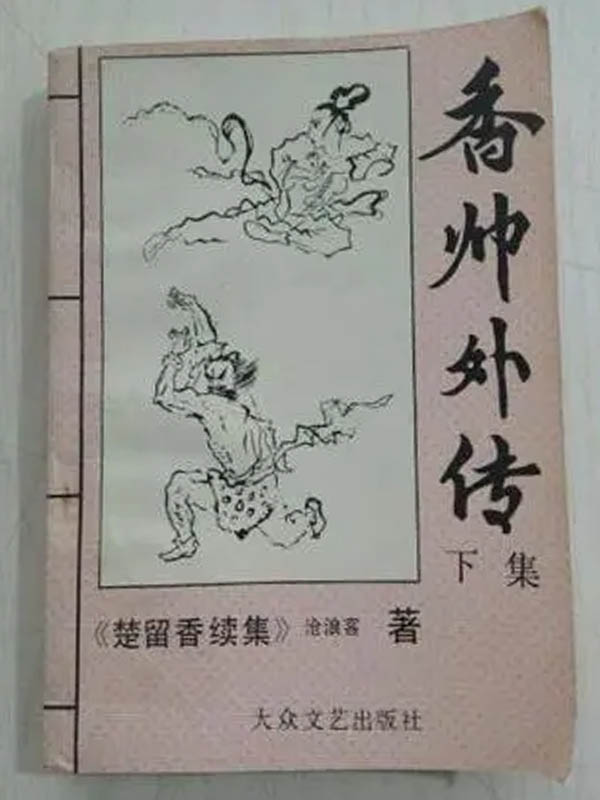目录

加入书架
小偷
工作室:苗疆公子发布作者:苗疆公子发布时间:2025-03-29
宁波府的春夜总带着咸腥的海风,张阿三蹲在飞檐翘角上,看着手中半块冷硬的芝麻饼叹气。瓦当上的貔貅石雕硌得他后腰生疼,更疼的是怀里那枚温热的和田玉佩——父亲临终前塞给他的最后物件,明日也要送进当铺了。
巷子里传来梆子声,三更天了。他正要翻身下房,忽然瞥见两点灯笼晃晃悠悠飘进巷口。两个皂衣汉子抬着顶青布小轿,轿帘掀开时闪过半张苍白的脸。张阿三的耳朵动了动,他听见轿中人腰间玉珏相撞的脆响,像极了他幼年时在苏州大户人家窗外听过的声音。
"张先生好雅兴。"轿中人开口竟是字正腔圆的官话,只是尾音带着奇怪的卷舌,"月下听风,可是在等有缘人?"
张阿三的后颈汗毛倒竖。他分明记得自己像壁虎般贴着墙根潜行,连野猫都没惊动半只。月光斜斜照在轿帘上,映出个梳着唐轮头的男人,三十上下,眉眼细长如工笔描画。
"阁下认错人了。"他压低草帽就要开溜,却见轿夫袖中寒光一闪。两柄倭刀出鞘的瞬间,他闻到了海风裹挟的铁锈味。
"五十两黄金。"男人从怀中掏出个织锦口袋,金锭相撞的声响让张阿三喉头发紧,"只要先生明日亥时,能从督军府西厢取件文书。"
瓦片在张阿三脚下发出细微的碎裂声。去年腊月他摸进过督军府厨房,光是绕过那十二个时辰轮值的亲兵就折了半条命。但五十两黄金...足够买下整条芙蓉巷的铺面。
"要偷什么?"
"不过是个黄杨木匣。"男人笑着展开折扇,扇面上泼墨山水间藏着几点朱砂,"匣中放着沿海卫所的换防文书,对先生来说易如反掌。"
子时的更鼓敲到第七下时,张阿三已经贴在督军府后院的银杏树上。这株百年老树虬枝盘结,正好够着他前日踩点的西厢房檐。今夜风急,树影婆娑如鬼手乱舞,反倒成了最好的掩护。
腰间的鹿皮囊里装着火镰、铁蒺藜,还有半包迷魂香——这是他去年从波斯商人那顺来的好货。瓦当上的青苔有些打滑,他像只壁虎般贴着屋脊挪动,突然听见檐下传来甲胄摩擦的声响。
两个亲兵举着灯笼转过月洞门,张阿三屏住呼吸。灯笼光扫过西窗时,他看见紫檀案几上果然摆着个黄杨木匣,铜锁上还缠着明黄绸带。这规制...分明是六百里加急的军机要件!
冷汗顺着脊梁滑进裤腰。坊间传闻倭寇最近在舟山岛外流窜,这换防文书若是落到...他猛然想起轿中人的卷舌音,胃里突然翻腾起来。但怀中的金锭沉甸甸地发烫,五十两黄金,足够他洗手不干回苏州买间茶楼。
迷魂香从窗缝飘进去半柱香后,张阿三撬开了雕花窗棂。月光漏进屋内,照亮木匣上"海防布阵图"五个朱砂小楷。他的手悬在铜锁上方微微发抖,父亲被倭刀砍断的右手突然在记忆里渗出鲜血——那年他八岁,躲在米缸里看着穿木屐的浪人烧了整条街。
"什么人!"院中突然炸响一声暴喝。张阿三抄起木匣撞破窗纸,碎木屑划破脸颊的瞬间,他听见弓弦嗡鸣。箭矢擦着耳畔钉入梁柱,亲兵们的脚步声如潮水般涌来。
他在屋脊上狂奔,瓦片在脚下噼啪碎裂。追兵的火把汇成一条赤蛇,箭雨掠过时带起的热风灼烧着后背。怀中的木匣突然变得千斤重,每跑一步都像是踩在父亲染血的草鞋上。
暗巷里的血腥气比海浪更先漫上来。张阿三捂着肋下伤口狂奔,身后倭寇的木屐声在青石板上敲出催命符。怀中的海防图像块烧红的烙铁,烫得他五脏六腑都在抽搐——方才藤原打开木匣时的狞笑,与他记忆中举着火把的浪人竟有七分相似。
"张桑果然守信。"两个时辰前,藤原在废弃盐仓验货时,拇指摩挲着图纸上金塘卫的标记,"不过..."倭刀出鞘的寒光惊起梁上栖鸽,"看过图纸的人都得死。"
若不是当铺老周给的硫磺粉,此刻他早成了甬江里的浮尸。张阿三拐进鱼市巷,腌货摊下翻出早备好的桐油桶。追兵踏入巷口的刹那,他踢翻油桶掷出火折子,冲天烈焰里传来皮肉焦糊的惨叫。
卯时的梆子声从城隍庙传来时,张阿三蜷缩在当铺地窖。老周掀开青砖递来汤药,忽然盯着他脖颈间的半块玉佩倒吸冷气:"这纹样...十年前倭寇屠村那夜,我在死人堆里见过!"
药碗坠地的脆响中,记忆如潮水破闸。八岁那年的月光也是这般惨白,父亲将他塞进米缸前,将染血的玉佩劈成两半。倭刀寒光闪过时,他看清了领头人嘴角的朱砂痣——与藤原耳后那点殷红分毫不差。
"劳驾周掌柜。"张阿三扯下玉佩拍在桌上,眼底燃着淬火的光,"烦请把库房那批受潮的火药,今夜亥时前运到望海塔。"
咸腥的海风里混进了硝石味道。张阿三蜷在望海塔顶层的斗拱之间,看着藤原的浪人队押着二十余个渔民登上礁石滩。潮水在嶙峋的黑色礁石间撕扯出白沫,像极了父亲被倭刀劈开时喷溅的血雾。
"张桑,这出戏您看得可还满意?"藤原踩着木屐踏上最高的礁石,手中倭刀挑开捆扎图纸的明黄绸带。海防图在暮色中哗啦展开,浪人们发出夜枭般的怪笑——他们永远不会知道,三个时辰前,当铺老周用半辈子修补古籍的手艺,早已将金塘卫的炮台位置改画成了鬼头礁。
张阿三的指尖摩挲着火折子。塔楼木梁上缠绕的引线浸过桐油,一直蜿蜒到堆在底层的二十桶受潮火药——老周说得对,这些结块的黑火药炸不开城墙,但足够让漫天纸屑烧成火雨。
"点火!"藤原突然暴喝。浪人举起火把逼近被捆的渔民,最前头的少年裤脚滴着水,正是那日鱼市巷帮他扶起油桶的卖蚶郎。张阿三的牙齿生生咬破下唇,血腥味混着火折子腾起的青烟灌进喉咙。
引线嘶叫着窜向塔底时,他想起昨夜潜入督军府的情景。总兵大人的亲兵统领将真图纸塞进竹筒时,居然冲他这个蟊贼抱了抱拳:"张义士若愿从军,这海防营斥候的位置......"
惊天动地的轰鸣掐断了回忆。整座望海塔像被巨灵神抡起的铁锤击中,燃烧的图纸碎片从爆裂的木窗中喷涌而出。赤红的纸蝶乘风掠过礁石滩,浪人们慌乱地扑打落在肩头的火苗,捆人的麻绳在混乱中被崩断的礁石割开。
"八嘎!"藤原的倭刀劈向卖蚶郎的瞬间,张阿三从塔顶残骸纵身跃下。怀揣的最后一包石灰粉在空中爆开,迷蒙白雾里他拽着少年滚进浪涛。咸涩的海水灌入口鼻时,他摸到腰间那个空荡荡的金线锦囊——五十两黄金买的桐油火药,到底比真金白银更烫手。
潮水将二人推上浅滩时,东边海平线已泛起蟹壳青。张阿三吐出嘴里的海沙,看见燃烧的鬼头礁方向升起三盏橘色孔明灯,那是老周说过的海防营得手的信号。卖蚶郎突然指着礁石群哭喊起来,顺着少年颤抖的手指望去,藤原的焦尸正卡在岩缝间,浪花拍打着他耳后那点朱砂痣,像要洗净二十年前就該干涸的血痂。
咸腥的海风卷着灰烬扑在脸上,张阿三用衣角裹住藤原焦尸手中的密信。火漆印上残缺的浪花纹让他太阳穴突突直跳——二十年前父亲带回的倭寇密函上,也有这般浪花纹。
"恩公小心!"卖蚶郎突然惊叫。张阿三本能地侧身翻滚,短刀擦着脖颈钉入礁石,刀柄上缠着的青藤绳结正是漕帮标记。十丈外的海蚀洞里,三个黑影正顺着岩壁急速攀援。
怀中的半块玉佩突然变得灼人。张阿三拽着少年躲进涨潮的浪涛,咸水浸透伤口时,他摸到玉佩背面经年被摩挲的凹痕——那根本不是吉祥纹,分明是浙东海疆的岛礁走势!
"周掌柜说过令尊是卫所画师。"两个时辰后,当铺地窖的油灯照亮老周手中的半片玉佩,"当年倭寇屠村,为的就是你爹刻在玉佩背面的暗礁水道图。"
记忆如惊雷炸响。八岁生辰那夜,父亲用银针在玉佩上刻下细纹,说这是给海龙王献宝的路引。此刻两半玉佩在桐油灯下严丝合缝,拼出的分明是双屿港暗流图——倭寇盘踞二十年的巢穴所在。
地窖木梯突然传来三急两缓的叩击声。卖蚶郎脸色煞白地冲下来,脖颈处的浪人刺青竟在烛火下泛着靛蓝幽光:"三桅船...鬼头礁东南五里..."
震耳欲聋的炮声打断了他的话。张阿三撞开当铺后窗,望见海天相接处炸开数团赤焰。三艘挂着商船旗的巨舰正在炮轰金塘卫瞭望塔,舰首的唐破风装饰在火光中宛如恶鬼獠牙。
"是铁甲舰!"老周手中的罗盘针疯狂旋转,"他们用假海防图调虎离山,真货轮趁着换防间隙..."
张阿三抓起浸过鱼油的麻绳缠在腰间,那枚拼合完整的玉佩硌在胸口发烫。父亲临死前瞪视倭寇首领的眼神穿越二十年光阴,此刻在他眼底重燃如炬。
金塘卫的炮台在暮色中化作燃烧的巨烛,张阿三站在父亲坠海的断崖上,掌心玉佩被铁甲舰的火光映得血红。老周连夜修复的明代福船正在浪谷间起伏,船头新装的火龙出水炮泛着冷光——那是用五十两黄金融铸的炮管。
"暗礁群在丑时三刻露出水面。"卖蚶郎突然扯开衣襟,靛蓝刺青在月光下竟浮现出潮汐密语,"恩公请看,这青雀纹的眼睛正对玉环岛漩涡。"
铁甲舰的第三发炮弹掀翻望海塔基座时,张阿三点燃了福船尾舵的火药箱。浸透桐油的船帆轰然张开,化作火凤凰扑向倭寇主舰。咸腥的夜风里,他听见二十年前父亲哼唱的采珠谣——原来那首小调里藏着暗礁群的生辰八字。
两船相撞的刹那,玉佩背面的礁石纹与海图重叠。铁甲舰龙骨折断的哀鸣声中,张阿三纵身跃入怒涛,怀中的硫磺筒在倭寇火药库上方炸开赤色漩涡。卖蚶郎的呐喊穿透海浪:"东北方三丈有父亲刻的逃生水道!"
三个月后的清明,新任海防把总在双屿港清点战俘时,发现倭寇秘库的青铜匣。匣中泛黄的《卫所志》记载:嘉靖十二年,画师张明远冒死刻暗礁图于佩,倭酋断其手而不得。
咸湿的海风吹过宁波府城墙,告示栏新贴的募兵榜被人用烧焦的倭刀刻了朵浪花。更夫说子夜常看见瘸腿汉子在城隍庙供半块残玉,香案上总搁着张泛潮的海防图——金塘卫炮台的位置,新添了道朱砂画的火凤。
 添加表情
添加表情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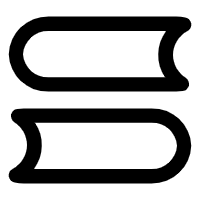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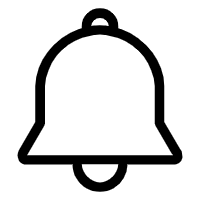 0
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