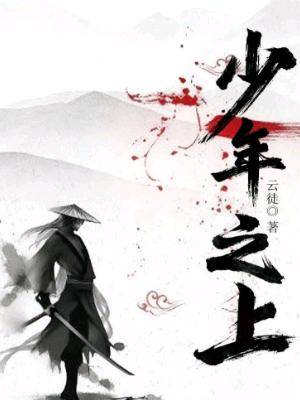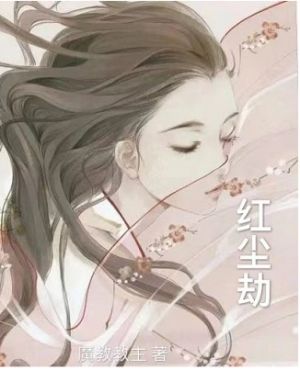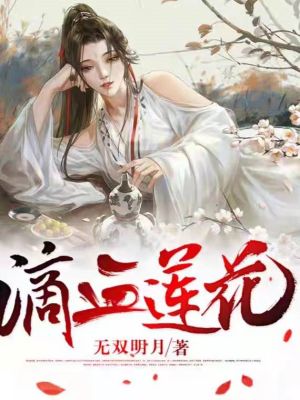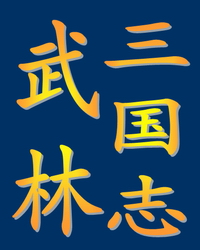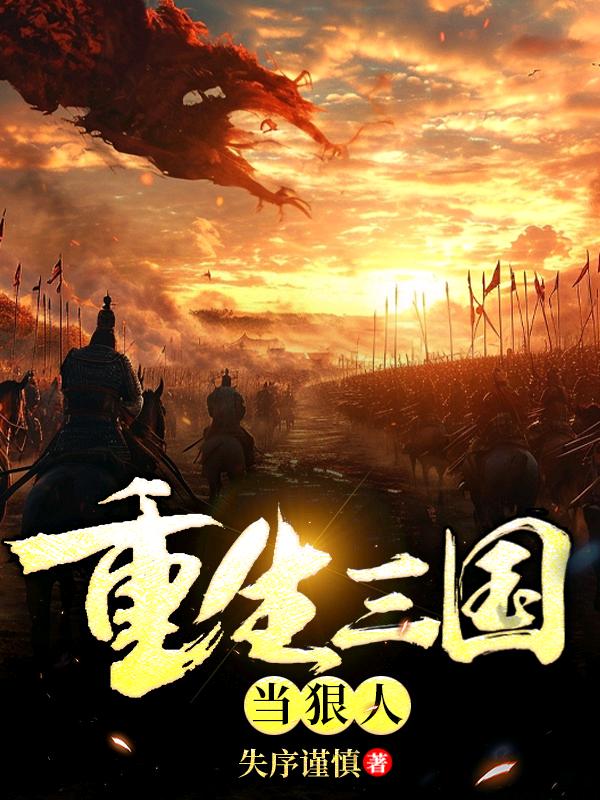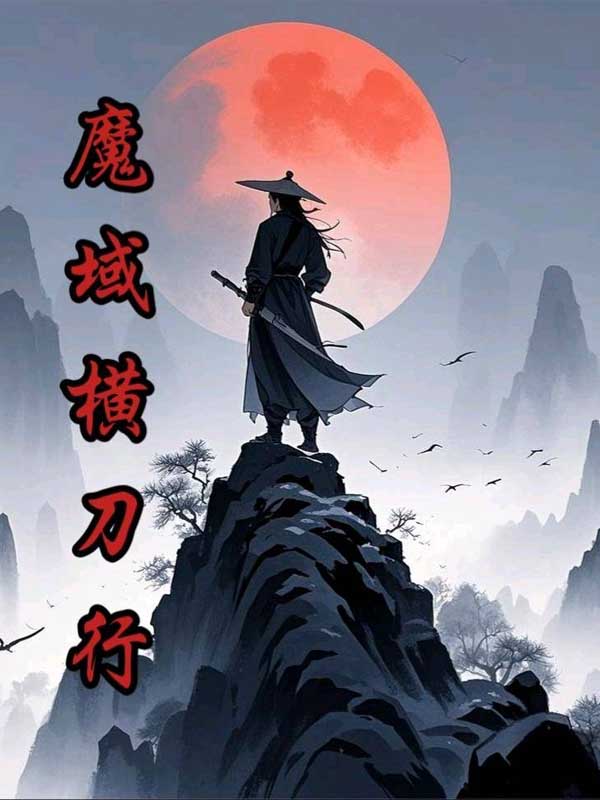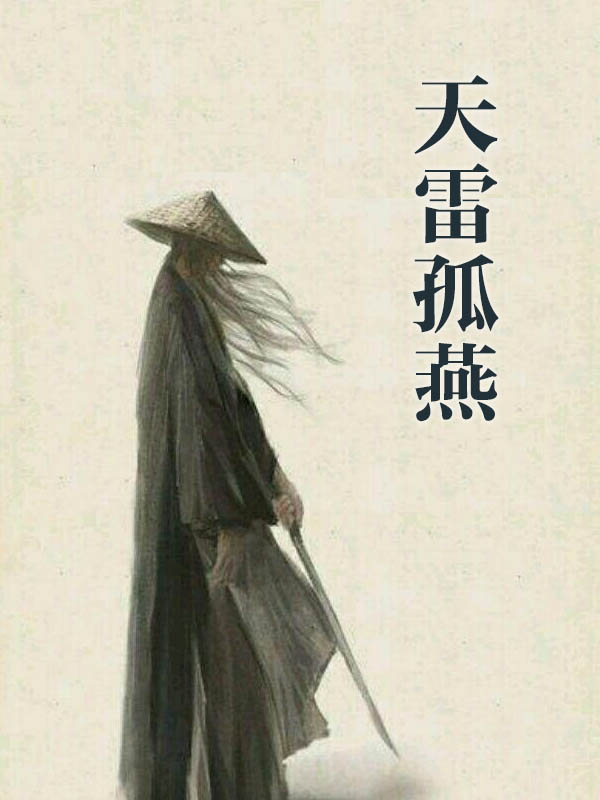目录

加入书架
棋子
工作室:苗疆公子发布作者:苗疆公子发布时间:2025-05-20
一、
细雨如丝,落在丞相府的青石板上。崔琰撑着一把油纸伞,站在回廊下等待召见。他望着院中那株老梅,枝干嶙峋如铁,在雨中更显孤傲。三年前,也是这样一个雨天,谢丞相在这株梅树下将他这个寒门学子提拔为幕僚。
"崔先生,丞相请您进去。"老管家低声唤道。
崔琰整了整衣冠,收起雨伞。水珠顺着伞骨滴落,在地上溅起细小的水花。他忽然想起今晨卜得的卦象——"泽水困",君子以致命遂志。
书房内,谢雍正在批阅奏折。烛光映照下,这位当朝丞相的面容显得格外威严。他已年过五旬,鬓角微霜,但双目如炬,不怒自威。
"属下参见丞相。"崔琰深深一揖。
谢雍放下朱笔,抬眼打量他:"子玉啊,太子府那边可有异动?"
崔琰心中一紧。三个月前,谢雍命他以太子宾客的身份潜入东宫,暗中监视太子的一举一动。这位寒门出身的谋士凭借过人才智,很快获得太子信任,得以参与机密。
"回丞相,太子近日频繁接见北境将领,似在谋划什么。"崔琰垂首答道,袖中的手微微颤抖。他隐瞒了一个关键信息——太子实则在筹划抵御北方蛮族入侵的边防策略。
谢雍轻抚长须,眼中闪过一丝冷光:"果然如此。明日早朝,陛下将宣布立储之事。"
崔琰猛地抬头。皇帝年迈多病,立储意味着权力更迭在即。他忽然明白了谢雍的用意——这位权倾朝野的丞相不愿看到与自己政见不合的太子继位。
"子玉,"谢雍的声音忽然柔和下来,"你可知我为何独独器重你?"
"属下愚钝,全赖丞相提携。"
谢雍起身,从书架上取下一个锦盒:"当年殿试,你的策论被考官评为'狂悖',是我力排众议将你留在身边。"他打开锦盒,取出一卷泛黄的纸页——正是崔琰当年的答卷。
崔琰眼眶发热。那年他二十出头,满腔热血写下改革朝政的方略,却差点因此断送仕途。是谢雍给了他出路,让他从一介布衣成为丞相府红人。
"明日午时,你带人去太子书房搜查。"谢雍的声音忽然转冷,"记住,要'仔细'搜查。"
崔琰心头剧震。这是要他栽赃陷害!他张口欲言,却见谢雍已背过身去,只留下一句:"退下吧,老夫乏了。"
雨更大了。崔琰站在丞相府门外,任由雨水打湿衣袍。三年来,他为谢雍出谋划策,铲除政敌,却从未像今日这般感到彻骨寒意。太子虽与谢雍政见不合,但勤政爱民,若因此遭构陷...
"崔先生,您的伞。"小厮追出来递上油纸伞。
崔琰恍若未闻,径直走入雨中。他想起昨日太子在书房对他说的话:"崔卿,若有一日本宫登基,定要废除门阀世袭之制,让寒门学子都有出头之日。"那一刻,太子眼中的真诚不似作伪。
回到寓所,崔琰彻夜未眠。天亮时分,他做出了决定。
午时将至,崔琰带着一队侍卫来到东宫。太子正在书房批阅奏章,见他带人闯入,面露讶色:"崔卿这是何意?"
"奉丞相之命,搜查东宫。"崔琰硬着心肠说道,目光却紧紧盯着太子。
太子神色骤变,随即苦笑:"原来如此。谢雍终于要动手了。"他起身推开书架后的暗格,"崔卿要找的,可是这个?"
暗格中赫然是一件绣着五爪金龙的袍服——这是谋反的铁证!崔琰倒吸一口冷气。他本以为需要自己栽赃,没想到太子竟真藏有违禁之物。
"这不是本宫的。"太子声音颤抖,"崔卿,有人要置我于死地。"
崔琰走近细看,发现龙袍针脚粗糙,布料却是宫中御用。他忽然明白了——这是谢雍派人提前放置的!如此精妙的布局,连他这颗棋子都被蒙在鼓里。
侍卫们已经发现了"证据",正欲拿下太子。崔琰厉喝一声:"且慢!"他转向太子,低声道:"殿下可信得过下官?"
太子凝视他片刻,重重点头。
"请殿下立即写下谢雍结党营私的罪状,下官有办法让这龙袍变成谢雍构陷储君的证据。"崔琰语速极快,"但要快,谢丞相的人随时会到。"
太子眼中闪过希望的光芒,立即挥毫泼墨。崔琰则从袖中取出早已准备好的谢府印信,小心翼翼地印在龙袍内衬上。
就在此时,外面传来喧哗声。谢雍的心腹带着禁军赶到,高呼:"奉旨捉拿谋逆太子!"
崔琰将伪造好的证据塞回暗格,转身迎向来人,脸上已换上肃穆表情:"下官已搜得铁证,请大人过目。"
三日后,朝堂震动。太子呈上的证据显示,龙袍实为谢雍派人放置,意在构陷储君。更令人震惊的是,崔琰当庭揭发谢雍结党营私、把持朝政的种种罪行。
谢雍被剥去官服时,死死盯着崔琰:"老夫待你不薄!"
崔琰垂目不语。直到谢雍被拖出大殿,他才轻声道:"丞相教导属下,为臣者当以社稷为重。"
一个月后,老皇帝驾崩,太子继位。登基大典上,新帝当众宣布崔琰为御史中丞,位列九卿。群臣纷纷道贺,唯有崔琰神色淡然。
是夜,崔琰独自来到谢雍被处决的刑场。月光如水,照在青石板上,那里还隐约可见暗红的血迹。他从怀中取出那卷当年谢雍保存的策论,就着月光点燃。
纸页化为灰烬,随风飘散。崔琰想起谢雍最后对他说的话——"你以为自己跳出了棋盘?殊不知,你我皆是棋子。"
次日早朝,宫人发现御史大夫的印信被整齐地放在衙署案头,而崔琰已不知所踪。有人说在江南见过一位酷似他的教书先生,也有人说他归隐山林。新帝派人四处寻找,终无所获。
只有那株丞相府的老梅,在来年春天开得格外绚烂。风吹过时,花瓣如雪纷飞,仿佛在诉说着那些无人知晓的权谋与背叛、忠诚与救赎。
二、
江南的雨总是来得突然。崔琰——如今化名林晏——放下手中的《论语》,望向窗外。雨水顺着茅草屋檐滴落,在青石板上敲出清脆的声响。兰溪村的孩子们刚下学,三三两两撑着油纸伞跑过泥泞的小路。
"先生,我娘亲做了桂花糕,请您尝尝。"扎着双髻的小女孩踮脚将油纸包放在窗台上,不等道谢就蹦跳着跑开了。
崔琰嘴角微扬。三年来,这种平淡如水的日子洗去了他身上的官场戾气。当初离开京城时,他烧毁了所有能证明身份的文牒,只带走了那方父亲留下的砚台。在这里,没人知道他曾是叱咤风云的御史中丞,孩子们只当他是从北方逃难来的落魄书生。
他拈起一块桂花糕送入口中,甜香在舌尖化开。忽然,远处传来马蹄声。崔琰的手指僵住了——这种整齐划一的蹄声,只能是训练有素的战马。
五匹黑马停在私塾门前,为首的青年男子一袭墨蓝锦袍,腰间玉带上悬着一柄古朴长剑。崔琰瞳孔骤缩,那剑鞘上的蟠螭纹他再熟悉不过——谢家祖传的"青霜"剑。
"林先生?"青年下马拱手,声音清朗,"在下途经此地,听闻先生学识渊博,特来请教。"
崔琰不动声色地打量来人。约莫二十五六岁,眉眼间依稀有谢雍的影子,但轮廓更为柔和。最令人心惊的是他行礼时左手压在右手上的姿势——这是谢家独有的礼数。
"乡野村夫,不敢当请教二字。"崔琰还礼,故意将右手压在左手上,"公子若不嫌弃,可进屋喝杯粗茶。"
青年眼中精光一闪,显然注意到了这个细节。他转身对随从道:"你们在外等候。"随即跟着崔琰进了草堂。
屋内简陋,唯有一案一榻,墙上挂着几幅未完成的山水。青年目光扫过案头砚台,突然道:"澄泥砚,产自绛州,是前朝贡品。寻常私塾先生用不起这等物件。"
崔琰沏茶的手稳稳当当:"祖上所传,让公子见笑了。"
"三年前,先父书房丢失了两样东西。"青年接过茶盏,指尖在杯沿轻轻摩挲,"一是崔琰的策论原稿,二是一方绛州澄泥砚。"
茶气氤氲中,两人四目相对。屋外雨声渐急,打在荷叶上噼啪作响。
"谢公子远道而来,不只是为寻一方旧砚吧?"崔琰终于开口。
谢峥——谢雍独子——放下茶盏,从怀中取出一卷绢帛:"先生请看。"
绢帛上是工笔绘制的《百官行述图》,详细标注了当朝各大臣的派系关系。崔琰一眼就看出四大世家——太原王氏、琅琊诸葛氏、陈郡袁氏、吴郡陆氏——已将朝政瓜分殆尽。而新帝的名字被画在一个金圈中,周围密密麻麻连着各色丝线,像只被困在蛛网中的蝶。
"陛下登基三年,如今沉溺酒色,朝政尽归世家。"谢峥声音低沉,"三个月前,北方大旱,朝廷拨的赈灾银两被层层克扣,到灾民手中不足十一。易子而食的惨剧,先生可曾听闻?"
崔琰眼前浮现出二十年前的景象——那年他九岁,家乡闹饥荒,父亲就是饿死在进京告御状的路上。他闭上眼:"谢公子欲如何?"
"清君侧,振朝纲。"谢峥斩钉截铁,"我知道先生恨先父,但如今能救天下的,唯有先生。"
崔琰突然笑了:"谢公子高看我了。一介草民,如何插手庙堂之事?"
"三日前,我已派人查清这村里二十七户人家的底细。"谢峥轻抚剑柄,"比如私塾东边的张家,其实是十五年前从江州逃来的杀人犯;西头的李家,儿子在海上做着走私生意..."
"够了!"崔琰拍案而起,茶盏倾倒,褐色的茶水在案上漫延,如同当年刑场上的血迹。
谢峥不慌不忙地从袖中取出一封信:"这是杜允之写给先生的密信。他如今任御史中丞,正是接替先生当年的位置。"
崔琰展开信纸,熟悉的字迹跃入眼帘:
「子玉兄台鉴:
朝局危矣。四大世家把持科举,寒门再无进身之阶。陛下连日饮宴,已半月不朝。北境告急,军报却被王党扣下...」
信末是一首小诗:「曾为棋子困局中,岂知棋手亦樊笼。劝君重拾屠龙术,莫负平生济世衷。」
雨水从茅檐漏下,滴在信纸上,晕开了墨迹。崔琰想起离京那日,杜允之在十里长亭送他时说:"子玉兄这一走,天下寒门学子又少一分指望。"
"三日后,我会启程回京。"崔琰终于开口,"但有一个条件。"
谢峥面露喜色:"先生请讲。"
"无论成败,不得牵连兰溪村民。"
"峥以谢氏列祖列宗起誓。"
当夜,崔琰做了个梦。梦中谢雍站在那株老梅下,手持黑子:"落子无悔,你可想清楚了?"他惊醒时,东方既白,案上《论语》被风吹开,正好是那句"知其不可而为之"。
三日后,一队商旅离开兰溪村。崔琰扮作账房先生,戴着斗笠跟在谢峥身后。过路的村民热情道别:"林先生早去早回啊!"孩子们追着马车跑了很远,直到官道转弯才停下。
崔琰没有回头。他知道,这一去,怕是再难回到这个世外桃源。车轮碾过黄土,扬起阵阵尘埃。远山如黛,云雾缭绕,恰似当年他第一次进京赶考时的景象。
七日后,京城。
崔琰站在醉仙楼二楼窗前,俯瞰朱雀大街的繁华景象。三年过去,京城更加奢靡。绸缎庄、珠宝铺鳞次栉比,歌楼酒肆笙歌不绝。一队华贵的马车缓缓驶过,车帘用金线绣着"王"字。
"那是王珣的侄女,昨日刚被册封为贵妃。"谢峥低声道,"为了这个位置,王家献上了三百万两白银充作军饷。"
崔琰皱眉:"北方战事吃紧?"
"岂止吃紧。"谢峥冷笑,"突厥可汗亲率十万铁骑南下,连破三州。而朝廷派去督军的,是王珣那个连马都不会骑的小儿子。"
正说着,楼下忽然骚动起来。一队官兵押着十几个衣衫褴褛的犯人走过,为首的军官高喊:"北境逃兵,按律当斩!"
囚犯中一个少年突然跪地哭喊:"我们不是逃兵!是将军自己先跑了,粮草断绝..."话未说完,就被军棍打晕过去。
崔琰握紧了窗棂。当年他辅佐太子时,最重视的就是边防建设。如今看来,三年心血已付诸东流。
"崔兄?"身后突然传来不确定的呼唤。
崔琰浑身一僵。这个声音...他缓缓转身,看到雅间门口站着个身着御史官服的中年男子,正是杜允之。
杜允之瞪大眼睛,手中的折扇"啪"地掉在地上:"果然是你!"
谢峥的手按上剑柄,崔琰微微摇头。杜允之快步上前,压低声音:"子玉,你疯了?现在满城都是谢家的暗探!"
"杜兄别来无恙。"崔琰拱手,"看来谢公子没告诉我全部实情。"
谢峥面露尴尬:"杜大人与先父...有些过节。"
杜允之冷笑:"何止过节?谢雍当年诬告我叔父贪墨,害得杜家满门抄斩。若非子玉兄暗中相救,我早成了刀下鬼。"他紧紧抓住崔琰的手,"你既已脱身,为何还要回来?"
崔琰望向窗外。囚犯们的血迹在青石板上拖出长长的痕迹,几个乞丐正趴在地上舔舐。
"为天下苍生。"他轻声道,自己都觉得这话虚伪得可笑。
杜允之盯着他看了良久,突然笑了:"好个'为天下苍生'!子玉啊子玉,你这爱说漂亮话的毛病还是没改。"他从袖中取出一卷竹简,"既然要演戏,总得知道剧本。这是王珣明日要呈给陛下的奏章副本,提议增加江南赋税。"
崔琰展开一看,数额竟是往常的三倍。"江南连年水患,再加赋税,百姓怎么活?"
"所以需要一位'故人'去提醒陛下。"杜允之意味深长地说,"明日午时,陛下会独自在御花园的沉香亭小憩。那是他唯一不带侍卫的时候。"
谢峥皱眉:"杜大人如何得知?"
"因为明日陪驾的袁贵妃,"杜允之露出狡黠的笑容,"是我表妹。"
崔琰与杜允之相视一笑,恍如回到了当年并肩作战的日子。窗外忽然雷声大作,暴雨倾盆而下。三人影子投在墙上,被闪电拉得很长,像三柄出鞘的利剑。
雨幕中,一个瘦小的身影匆匆跑过醉仙楼下。崔琰眯起眼睛——那是个十来岁的小太监,怀里紧紧抱着什么,不时回头张望。突然,一队禁军从巷口冲出,小太监慌不择路,竟朝醉仙楼方向跑来。
"那是...陛下身边的如意?"杜允之脸色骤变。
崔琰二话不说冲下楼去。在禁军即将抓住小太监的瞬间,他一把将人拉进醉仙楼后厨。
"救、救救奴才..."小太监满脸是血,从怀中掏出一个沾血的荷包,"陛下...陛下有危险..."
荷包里,是一枚带毒的银针和半块被血浸透的玉佩——上面赫然刻着"谢"字。
三、
血从荷包渗出,在崔琰掌心留下黏腻的触感。醉仙楼后厨的灶火噼啪作响,小太监如意的呼吸越来越弱。
"谁要杀陛下?"崔琰压低声音问。
如意颤抖的手指在血泊中划出半个"王"字,突然瞳孔扩散,头歪向一边。崔琰探他颈脉,已然气绝。门外禁军的脚步声越来越近。
"这边搜!"粗犷的男声伴随着刀鞘撞击铠甲的声音。
杜允之闪身进来,见状倒吸一口冷气:"这是陛下贴身内侍,怎会..."
崔琰迅速将荷包和玉佩塞入袖中,扯下如意腰牌:"杜兄,可有密道?"
"跟我来。"杜允之推开柴堆,露出一个狗洞大小的暗门,"这是醉仙楼老板走私用的。"
三人匍匐爬过狭窄的暗道,来到一间地下酒窖。谢峥点亮火折子,昏黄的光线下,数百个酒坛整齐排列,散发着浓郁的酒香。
崔琰展开荷包,那枚银针在火光下泛着诡异的蓝光。"牵机毒,"他沉声道,"见血封喉。"
"这玉佩..."谢峥脸色煞白,"是家父随身之物,但三年前就已随葬。"
杜允之冷笑:"好个栽赃嫁祸!王珣这是要一石二鸟——除掉陛下,再嫁祸谢氏余党。"
崔琰摩挲着玉佩断裂处:"不对。这玉质地温润,是上好的和田玉,但谢公生前佩戴的应是蓝田玉。"他看向谢峥,"令尊可曾将玉佩赠人?"
谢峥思索片刻,突然拍案:"先父曾将半块玉佩赠予北境大都护李崇!说是年轻时结拜的信物。"
"李崇..."崔琰瞳孔骤缩,"现任北境大都护不是王珣的侄子王焕吗?"
"三年前陛下登基后,李崇就被调回京城,后来..."谢峥声音渐低,"暴毙家中。"
酒窖陷入死寂,只听得见三人急促的呼吸声。崔琰脑中闪过无数碎片:北方战事、失踪的军报、暴毙的将领、如今的暗杀阴谋...一切渐渐连成一线。
"王珣要谋反。"崔琰断言,"北方战败是假,借突厥之力逼宫是真。若陛下驾崩又无子嗣..."
"琅琊王是王珣外甥。"杜允之补充道,"按祖制可继大统。"
谢峥一拳砸在酒坛上:"必须立即面见陛下!"
"来不及了。"崔琰盯着银针,"如意拼死送出这消息,说明刺杀就在今日。杜兄,袁贵妃可靠吗?"
杜允之苦笑:"她是我表妹不假,但入宫三年...我只能说试试。"
"那就赌一把。"崔琰从怀中取出一个小瓷瓶,"我这里有颗'回阳丹',可解百毒。谢公子,你速去联络谢家旧部,在玄武门外候命。杜兄,想办法让我进宫。"
杜允之思忖片刻,突然眼睛一亮:"太医署今日当值的刘太医,是家父故交。他可帮你混进去。"
一个时辰后,崔琰换上青色官袍,戴着刘太医的面具,跟随杜允之进入皇城。午时的阳光炙烤着朱红宫墙,侍卫的铠甲反射出刺目的光。崔琰手心渗出冷汗——三年前他就是从这里逃离,如今却要自投罗网。
"刘大人,"宫门守卫拦住去路,"今日不是您当值吧?"
杜允之上前一步:"陛下昨夜饮宴受凉,贵妃特召刘太医诊治。"
守卫狐疑地打量着崔琰,突然伸手要揭他面具。千钧一发之际,一个清冷的女声从身后传来:
"怎么,本宫的话也不管用了?"
一顶华美的凤辇停在宫门前,帘子掀起一角,露出半张倾国倾城的脸。崔琰连忙躬身:"参见贵妃娘娘。"
袁贵妃——杜允之的表妹——慵懒地挥挥手:"还不快进来,等着陛下病情加重吗?"
守卫慌忙放行。凤辇内,袁贵妃示意崔琰靠近:"杜表哥说你有办法救陛下?"她声音极轻,"陛下今早咳血,现在沉香亭昏睡,身边全是王珣的人。"
崔琰心头一紧:"娘娘可信得过御前侍卫统领赵戬?"
"赵将军三日前被派去北境'督军'了。"袁贵妃冷笑,"接任的是王珣的妻弟。"
凤辇穿过重重宫门,最终停在一处僻静小径。"前面就是沉香亭,"袁贵妃递来一块玉牌,"凭此可近陛下身。记住,你只有一刻钟时间。"
崔琰深吸一口气,拎着药箱走向那座被垂柳环绕的亭子。八名带刀侍卫分立两侧,亭中隐约可见一个明黄身影倚在榻上。
"站住!"侍卫长横刀阻拦,"陛下有令,任何人不得..."
崔琰亮出玉牌:"贵妃娘娘命臣为陛下请脉。"
侍卫长查验玉牌,不情愿地让开道路。崔琰缓步走入亭中,终于见到了三年未见的皇帝——曾经那位意气风发的太子。
眼前的男人面色灰败,眼窝深陷,明黄龙袍松松垮垮地挂在身上,哪里还有当年锐气?听到脚步声,皇帝微微睁眼:"爱卿...又是来送药的?"
崔琰跪下把脉,心中大惊——脉象沉涩紊乱,分明是长期中毒之兆!他悄悄取出回阳丹:"陛下,请服下此药。"
皇帝突然抓住他的手腕,浑浊的眼中闪过一丝清明:"你不是刘太医...你是..."他猛地瞪大眼睛,"崔琰?!"
亭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。崔琰顾不得许多,低声道:"陛下,王珣要谋反,北方军情危急,您已中毒多时..."
"朕知道。"皇帝苦笑,从枕下抽出一封密信,"李崇死前送来的...但朕...无能为力..."他突然剧烈咳嗽,袖口染上点点猩红。
崔琰迅速将回阳丹塞入皇帝口中:"陛下务必保重,臣等自有安排。"
"来不及了..."皇帝艰难地指向亭柱,"暗格...虎符...去找..."话未说完,突然昏死过去。
"陛下!"亭外侍卫闻声冲来。
崔琰急中生智,高声喊道:"快传太医令!陛下旧疾复发!"同时手指飞快摸索亭柱,果然触到一处暗格。他刚将里面的物件塞入袖中,就被侍卫架起拖出亭外。
"你是何人?"侍卫长厉声喝问,一把扯下崔琰面具。
崔琰索性不再伪装:"御史中丞崔琰,有要事面奏陛下!"
"崔琰?"侍卫长大惊失色,"三年前畏罪潜逃的那个?来人啊,抓刺客!"
崔琰猛地撒出一把药粉,趁众人视线模糊之际,撞开两名侍卫夺路而逃。身后警哨声四起,数十名禁军从四面八方涌来。
他拐过假山,突然被一只有力的手拽入暗门。杜允之捂住他的嘴:"别出声!"
逼仄的密道中,两人屏息听着外面杂沓的脚步声。崔琰这才发现袖中物件是半枚青铜虎符——可调动京城三万禁军!
"王珣发现虎符失窃,定会全城搜捕。"崔琰低声道,"必须尽快出宫。"
杜允之却摇头:"出不去了。王珣已下令封闭九门,说是捉拿刺杀陛下的谢氏余党。"他苦笑,"你猜他们在谁府上搜出了'证据'?"
崔琰心头一沉:"谢峥..."
"不止。"杜允之递来一张纸条,"刚收到的信鸽。北方五州已失陷,突厥大军距京城不过三百里。而王珣...今早已派使者秘密前往敌营。"
崔琰握紧虎符,忽然明白了皇帝那句"去找"的含义。这半枚虎符需要与另外半枚合二为一才能生效——另半枚应在北境大都护手中。但如今的大都护是王焕...
"杜兄,可敢再赌一次?"崔琰眼中燃起决绝的火光。
杜允之大笑:"三年前你离京时,我说过什么?'杜某此生,唯君马首是瞻'。"
两人沿密道来到一处偏僻冷宫。崔琰从药箱底层取出易容工具:"我需要扮成一个人——已故的北境大都护李崇。"
"你疯了?李崇已死三年!"
"正因如此,王焕才认不出真假。"崔琰开始往脸上粘贴胡须,"王焕从未见过李崇真容,只知道他是个须发花白的老将。我要用这半枚虎符,骗他交出另半枚。"
杜允之目瞪口呆,随即抚掌大笑:"妙计!但如何出城?"
"袁贵妃。"崔琰已装扮完毕,俨然一位六旬老将,"她既能帮我入宫,必能帮我出城。"
黄昏时分,一队禁军护送着"李崇"的马车疾驰出玄武门。守卫本欲阻拦,车帘掀起一角,露出袁贵妃的玉牌:"奉陛下密旨,送李将军连夜赴任。"
马车刚出城三里,突然被一队黑衣人截住。崔琰暗扣袖中匕首,却见为首者揭下面巾——竟是谢峥!
"崔先生,"谢峥浑身是血,却笑容灿烂,"谢氏旧部三百死士,已候多时。"
远处,京城方向火光冲天。崔琰眺望良久,轻声道:"开始了。"
夜幕下,一支铁骑正向京城疾驰而来,马蹄声震得大地微微颤抖。旌旗在月色中隐约可见——不是突厥狼旗,而是北境军的玄色鹰旗。
崔琰握紧虎符,忽然想起谢雍那株老梅。不知今夜过后,又有多少鲜血要染红京城的土地?他望向身旁的谢峥和杜允之,三人相视一笑,一切尽在不言中。
车轮滚滚,向着北方疾驰而去。崔琰知道,真正的棋局,此刻才刚刚开始。
四、
北风卷着细雪拍打在崔琰脸上,生疼。他站在北境军大营外,铁甲下的衣衫早已被冷汗浸透。扮演已故三年的李崇,这计划疯狂得近乎自杀。但当他看到营门上悬挂的北境军旗——黑底金鹰,边缘已经破烂——突然有了把握。
"李大都护到!"哨兵高声传报。
崔琰挺直腰背,让花白胡须在风中飘扬。他刻意跛着右脚——杜允之说过,李崇当年在雁门关受过箭伤。营门缓缓开启,火把的光亮中,一个身披狐裘的年轻将领快步迎来。
"末将王焕,参见大都护!"
崔琰眯眼打量这个王珣的侄子。不过二十五六岁,面容白皙得不像边关将领,唯有虎口的老茧说明他确实习武。更令人意外的是他眼中的狂热——不是对权力的渴望,而是某种近乎虔诚的期待。
"免礼。"崔琰刻意压低嗓音,模仿北方口音,"军情紧急,进帐说话。"
中军大帐内炭火熊熊,却驱不散崔琰骨子里的寒意。王焕亲自斟酒:"大都护诈死三年,必是奉了陛下密旨。如今时机成熟了?"
崔琰心头一跳。诈死?密旨?他不动声色地饮尽杯中酒:"虎符带了吗?"
王焕从怀中取出一个锦囊,倒出半枚青铜虎符:"只待大都护手中那半枚..."
帐外突然传来喧哗。一个满身是血的斥候冲进来:"将军!京城急报,王大人命您立即回师勤王,说是谢氏余党勾结突厥谋反!"
崔琰握紧了袖中的虎符。王焕却出人意料地笑了:"果然如此。"他转向崔琰,"大都护可知,三日前突厥可汗已与我军秘密议和?"
"议和?"崔琰真惊讶了。
"用这个。"王焕从案下取出一颗人头——正是突厥左贤王!"谢峥公子亲自潜入敌营取的。作为交换,我们要帮他清君侧。"年轻人眼中闪烁着异样的光芒,"当然,这一切都是奉陛下密旨。"
崔琰脑中电光石火般闪过无数碎片:谢峥的异常镇定、北境军的突然回师、王焕对"李崇"的热情...一切都有了解释。这不是谋反,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变!
"虎符。"崔琰终于取出自己那半枚,"合二为一,即刻发兵。"
两半虎符相扣的瞬间,严丝合缝。王焕单膝跪地:"请大都护下令!"
崔琰深吸一口气。这一刻,他不再是棋子,而是执棋者。"传令三军,兵分两路。你率主力佯攻东门,我带精骑从玄武门密道入城。"
"得令!"王焕起身击掌,帐外立即涌入十余名将领。崔琰倒吸一口冷气——这些都是当年太子府的旧部!
雪越下越大。崔琰率领三千铁骑向京城疾驰,黑色斗篷在身后猎猎作响。谢峥骑马跟上,脸上是掩不住的兴奋:"崔先生,一切按计划进行!"
"什么计划?"崔琰冷声问,"你何时与北境军联络的?"
谢峥大笑:"三年前先父被处决那日。王焕表面是王珣侄子,实则是先父安插的暗棋。"他从怀中取出一封信,"这是先父遗命,要我伺机清除世家,还政于陛下。"
崔琰扫过信笺,上面谢雍的字迹力透纸背:「...世家误国,尤以王氏为甚。为父忍辱负重二十载,终不得志。吾儿当继此志...」
雪花落在信纸上,融化成小小的水渍,像极了眼泪。崔琰忽然明白了谢雍临终那句"你我皆是棋子"的真正含义——连谢雍自己,也不过是更大棋局中的一枚弃子。
玄武门在望。崔琰高举虎符,守军立即打开侧门。杜允之早已候在门内,脸色惨白:"快!陛下快不行了!"
皇宫一片混乱。崔琰带人直奔寝宫,沿途侍卫纷纷倒戈加入。当他们踹开寝宫大门时,只见王珣正掐着皇帝的脖子,袁贵妃倒在血泊中,手中还紧握着那枚带毒的银针。
"逆贼!"王珣拔剑指向崔琰,"你..."
谢峥一箭射穿他手腕。禁军一拥而上,将这位权倾朝野的尚书令按倒在地。崔琰冲到龙榻前,扶起奄奄一息的皇帝。
"爱卿...来了..."皇帝嘴角溢出血沫,"朕...对不起你..."
崔琰握住那双枯瘦的手:"陛下安心,四大世家已伏诛,北境大捷。"
"好...好..."皇帝艰难地从枕下取出一道密旨,"传位...琅琊王...崔卿...为顾命大臣..."话未说完,手臂颓然垂下。
崔琰展开密旨,上面清清楚楚写着要废除门阀世袭、开科取士的新政纲领。原来皇帝并非昏庸,只是被世家钳制,暗中一直在筹划改革。
"崔先生?"谢峥轻声唤道,"接下来..."
崔琰合上密旨,看向窗外。东方既白,新雪覆盖了宫墙上的血迹,仿佛一切罪恶都被洗净。他突然觉得无比疲惫。
三日后,琅琊王继位,崔琰官复原职,加封太子太傅。朝堂之上,新帝拉着他的手说:"朕年幼,全赖太傅辅佐。"
崔琰跪拜还礼,目光却与站在武官行列的谢峥相遇。年轻人眼中闪烁着野心的光芒,与当年的谢雍如出一辙。
当夜,崔琰独自来到谢雍被处决的刑场。月光如水,照在青石板上。他从怀中取出那方澄泥砚,轻轻放在地上。
"丞相,这一局,算和棋如何?"
次日清晨,宫人发现太子太傅的印信整齐地放在案头,人已不知所踪。谢峥派人四处寻找,终无所获。
只有兰溪村的孩子们知道,他们的林先生在一个雪夜突然回来了,带回许多新书和一块漂亮的砚台。私塾重新开张那天,老梅树上最后一片花瓣悄然飘落,仿佛在为远方的京城唱一曲无声的挽歌。
 添加表情
添加表情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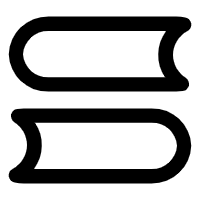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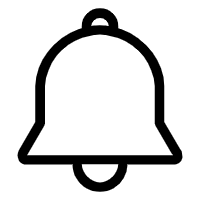 0
0